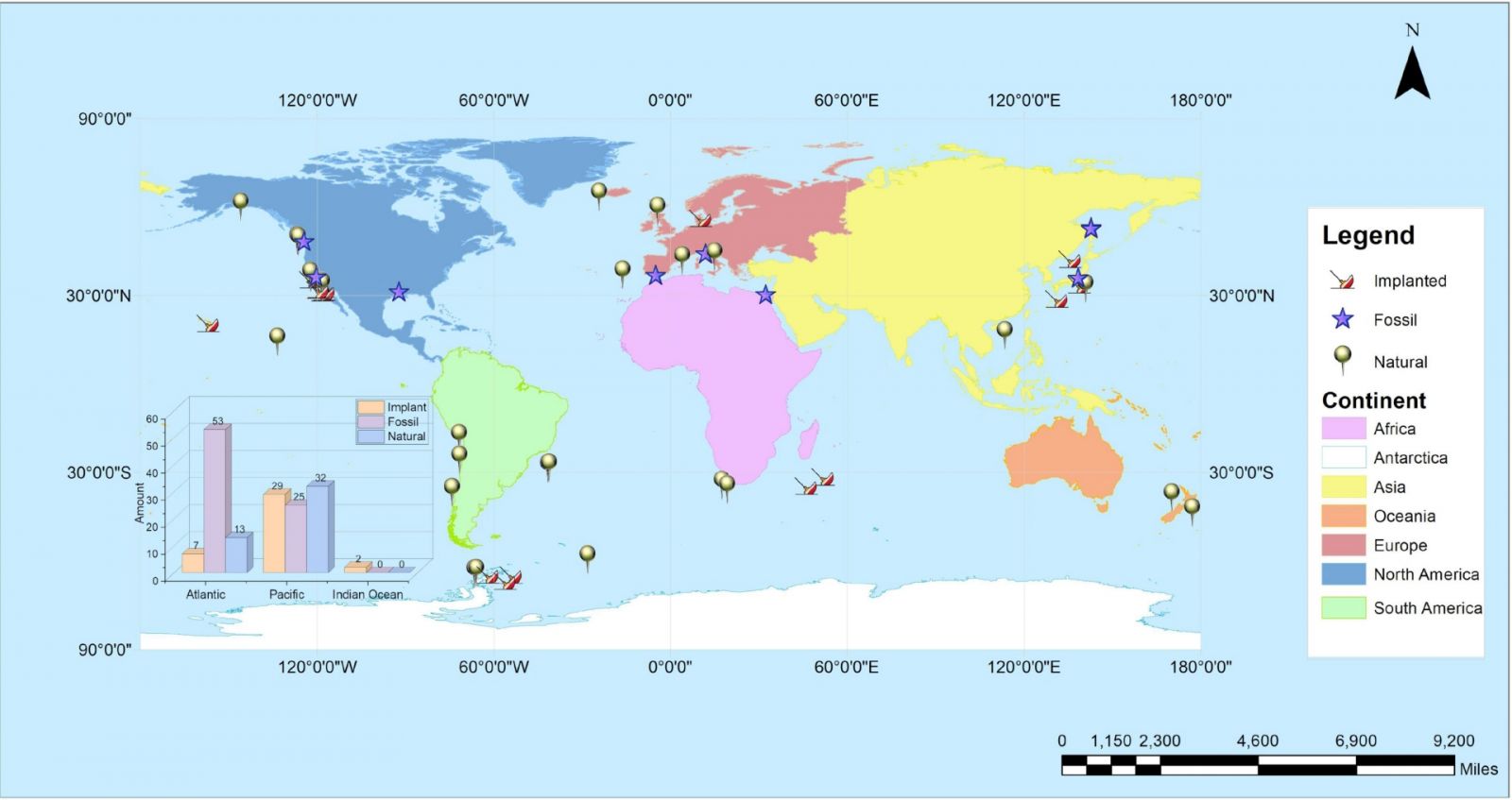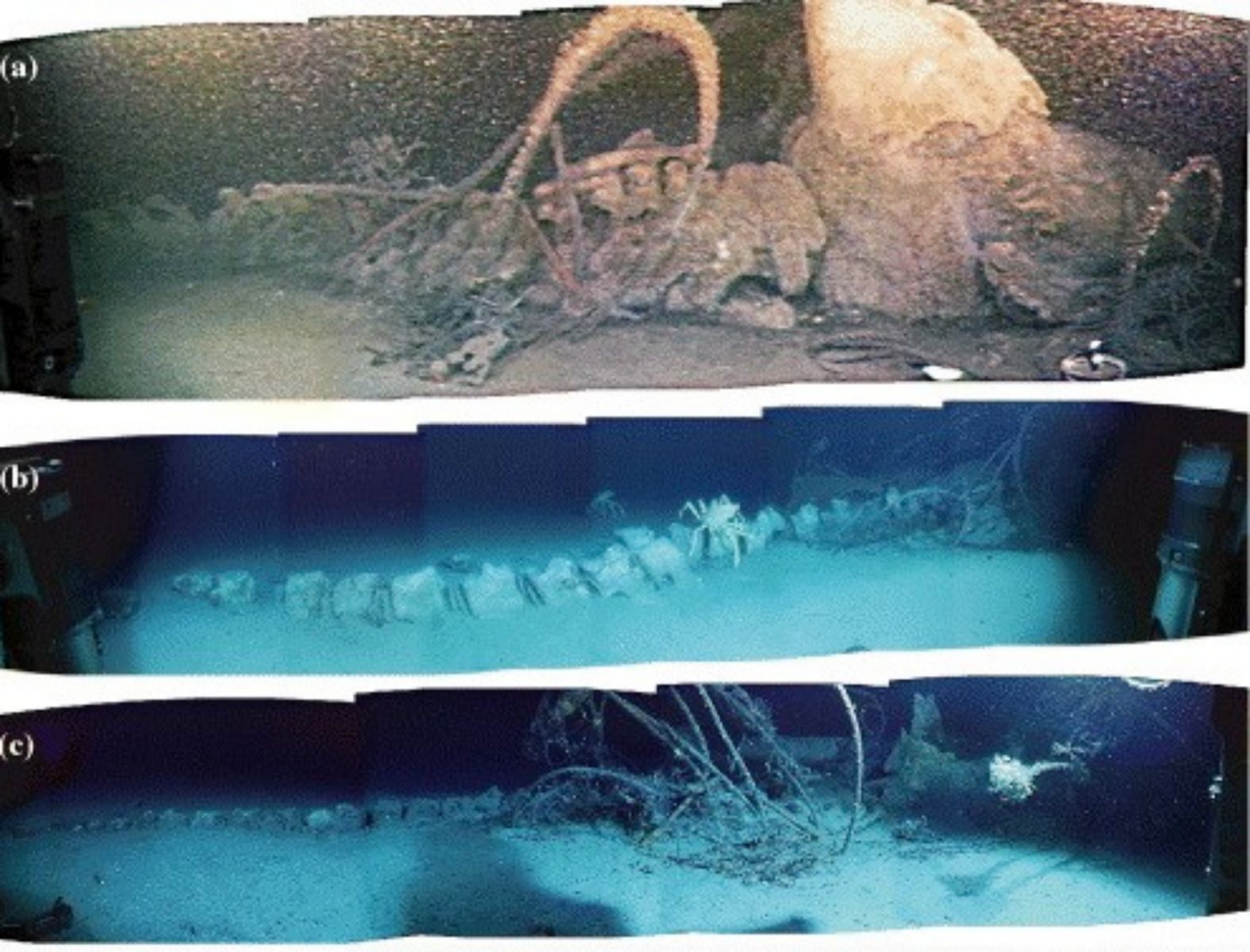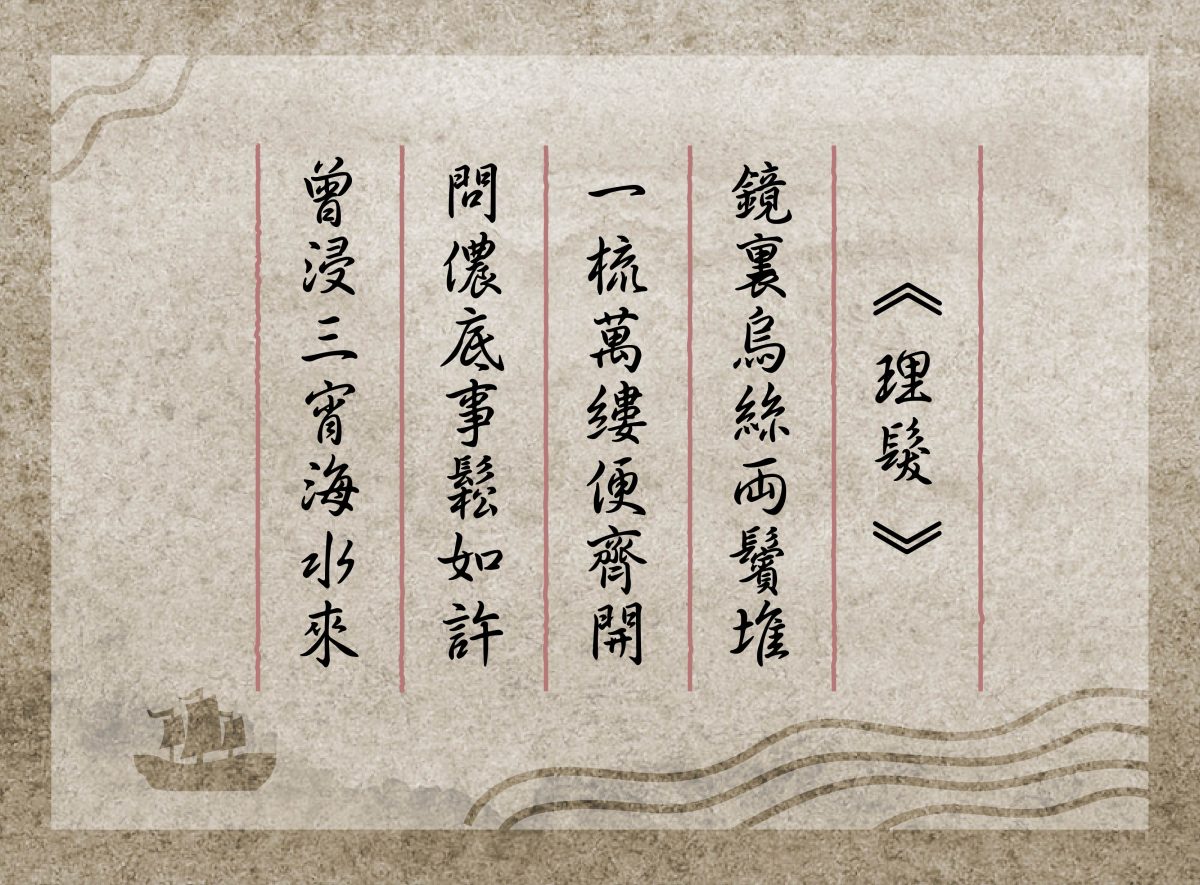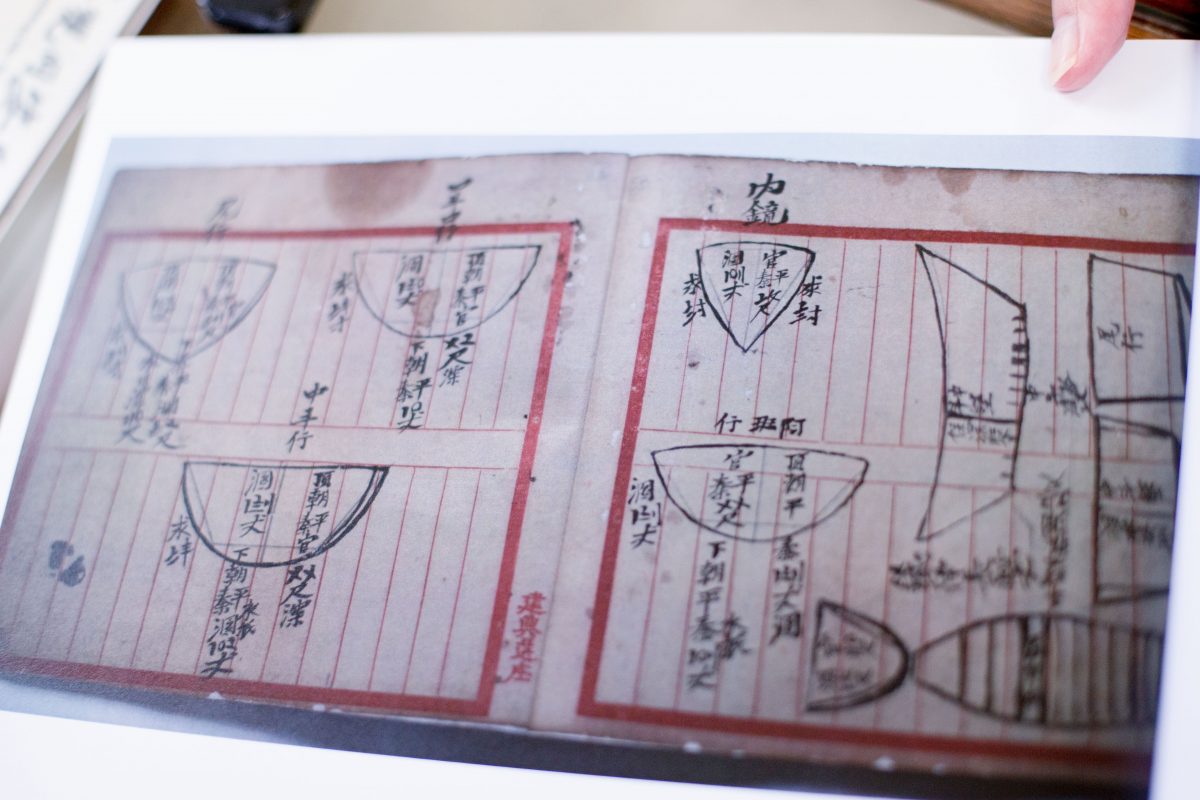作者/趙軒翎(科學月刊編輯)
2014年謝志豪升等為台大海洋研究所教授,2015年7月又榮獲日本第18屆生態學琵琶湖獎的殊榮。他結合理論模型、野外調查實務數據與統計分析等跨領域科學方法,解決湖泊及海洋生態系統中漁業、優養化與環境變遷問題,而獲得此獎的肯定。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位於校園的西北角,醉月湖的北岸,左右有天文數學館與凝態中心暨物理系館兩棟新的高樓矗立,襯托之下,海洋所的大樓顯得多了些歷史的痕跡,這裡就是謝志豪副教授任職之處。進入四樓的研究室,我們遇到的是如同實驗室中大學長般親切、沒有拒人之外學者架子的謝志豪老師,這樣一位年輕學者卻已有多篇令人驚豔的論文發表在世界頂尖的期刊上,讓人不能不好奇他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分生年代抵抗分生
雖然達到錄取醫學系的成績,卻寧可就讀台大動物系,謝志豪笑著說當時許多進入動物系的學生都是這樣。他進入台大就讀的那年,民國82 年,正好是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生物醫學研究所相繼正式成所的時代,在相關人士的宣揚與媒體的播送下,分子生物學成為當時台灣的顯學。在這樣的氛圍下,吸引了許多像謝老師這樣的學子進入生物相關科系就讀,期望能在這個尖端的生物研究中有所突破,進而貢獻生技產業或是醫學領域。
不過到了大二升大三的暑假進入實驗室後,他發現自己總是做不好分生實驗,搞不定這些儀器和技術。雖然實驗室的學長安慰他,犯完所有可以犯的錯誤之後,一定可以海闊天空、駕馭自如,但這樣的挫折卻仍讓他覺得自己不適合這樣的研究方向。
直到他跟著教授無脊椎動物學的陳俊宏老師,到澎湖去做野外實驗,在海邊採集樣本,他至此萌發了對生態的喜愛與熱情。而後又有幸遇到石長泰和丘臺生老師,帶領他進入浮游生物的世界。關起分子生物的這扇門後,生態的這扇窗開啟了,每個月出海採樣、努力學習浮游生物種類鑑定。謝志豪說,雖然要用很小的鑷子在顯微鏡下解剖微小的浮游生物,但對他而言卻比分生實驗容易上手。
研究所時想選擇純粹的海洋生態研究,不要再有分生實驗的實驗室。但在當年那個研究氛圍下可說是難上加難,因為連生態學都面臨分生的新研究工具引進而導致的轉型壓力。最後他選擇了與石長泰、丘臺生兩位海洋生態學家,學習如何研究台灣海峽的浮游生物與漁業資源。
讀論文是興趣
難道不跟著分生的潮流,就只能沉浮於傳統生態學領域?謝志豪可不這麼認為,他勇於跨入了另一個他不那麼熟悉的領域,並將生態學與這個領域做緊密的連結,這個領域是「數學」。生物統計及生物數學在現在可能不是一個新興的概念,但當時台灣在這方面的研究卻落後許多。他笑著說,當時會唸生物科系的通常數學不太好,或者是覺得自己數學不太好。不過開始想用數學作為研究工具,但數學又不好怎麼辦?於是他開始去旁聽數學系的課程,接觸微分方程、高等微積分,並且自己學寫程式,一點一滴唸下來,才發現是自己把數學想得太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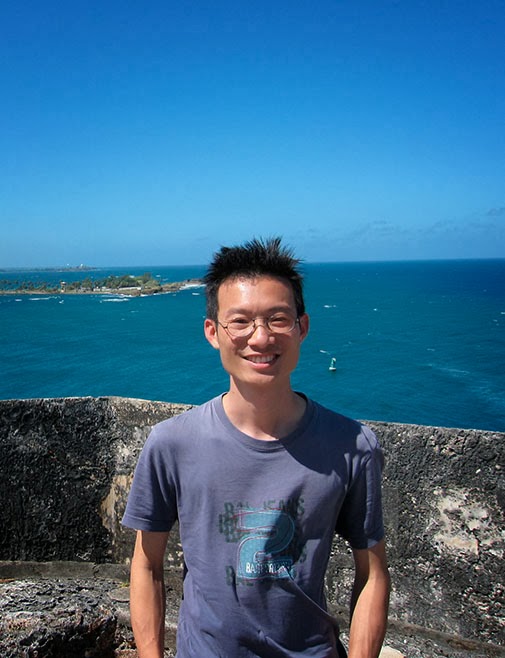
多數的研究生把大多數的時間花在自己的論文題目上,他卻將大把時間拿來了解各種不同的領域,他說讀論文是他的「興趣」。當他對某個主題有興趣,他會去念這個主題相關的論文,其中遇到不懂的或有疑問的,就再去閱讀更多的論文。「我想知道它的來龍去脈,我對歷史很有興趣,我會想知道誰是第一個提出這樣的想法的人,為什麼想這樣解決問題。」謝志豪的語句中很自然的流露他渴望更多新知識、新觀念的熱情,在這樣的過程中,他不僅擴充他的學識範圍,這些求知經驗更在一點一滴的累積下,成為他現在課堂上授課的題材。
進入理論生態殿堂
碩士畢業後他申請上了相當著名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前往美國就讀博士班。「我跟我的老闆馬克歐曼(Mark Ohman)說我不要做種類鑑定,這我已經會了,我想做洋流模型,看洋流的流動如何影響生物漂送及族群變動。」也因此謝志豪走入理論生態學,由一本《生態學入門》(A Primer of Ecology)和程式設計課本開啟了新領域的門。從大學、碩士班累積起來的數學也沒有荒廢,他每個學期必定修一門數學系或機械系大學部的數學課,他打趣地說,「上過國外的數學課,才發現台灣的數學課,對於非數學專業領域的學生而言,真的教太難了,不是學生太笨!」
因為他的認真與努力,也讓他遇到了影響他博士班生涯的第二位老師,杉原(George Sugihara)教授。謝志豪回憶道,「我去上他的計量生態學,別的同學交作業都是紙本,我都寫程式,老師每次給我的成績上都寫Super !他改成績的方式就是ok、good、excellent、super 分級, 沒有分數。」好的表現使杉原教授對謝志豪印象深刻,並將他挖角到自己的實驗室。
這個轉換讓謝志豪相當掙扎,一來是原實驗室的歐曼教授是帶他走入理論生態領域的重要老師,給他很多激勵和幫助,且當時已經準備要提博士資格考了。二來是他懷疑自己有沒有這個能耐,可以去應付新研究課題的挑戰。當他下定決心與舊實驗室道別時,他的理由是,「我認為我現在做的研究題目不夠具有挑戰性」,看似一句相當直接、大膽的話背後,其實有相當多的考量。
「當我在念碩士班時,像洋流模型這樣的題目全世界只有十個人在做,但當我唸博士班時卻有一百人會做,且出現了很多軟體,若我不能自己去發明軟體,那我就只是學會使用軟體和調整參數,這並非我讀博士班的初衷。」他決定給自己更新的挑戰,這種「除了要好,還要更好」的態度,相信是他不斷突破自我的動力,不過這次的轉換跑道卻也帶給他意想不到的艱難磨練。
他成為了兩個教授共同指導的學生,雖然這不是很特別的案例,但當發現這兩個教授對彼此頗有意見後,夾在中間的學生就相當尷尬了。兩位教授都是學生公認非常嚴格的老師,能在這兩位嚴師指導下順利畢業,謝志豪笑著說自己成了系上的「傳奇人物」。
雖然謝志豪一直都以輕鬆的語氣敘述這段經歷,卻不難想見當時他所面臨的壓力與挫折。博士班三年級他得重新構思研究題目,老師卻又一直不滿意他提出的想法,此外公費留學的獎金也即將用罄,卻沒有經費來源。在什麼都沒有的窘困情況下,曾讓他非常後悔轉換實驗室的念頭。

獲得漁業寶庫
幸運的是,他遇到了一位準備從美國西南漁業中心(Southwest Fisheries Science Center, NOAA)退休的老教授約翰(John Hunter)。約翰手中有一筆累積50 年的加州魚類資料,想找人幫他分析這些資料,希望對漁業有幫助。他說「I should give this treasure to a good hand」,而謝志豪則成為這雙「good hand」。
「他們想從資料庫中找到生態指標(ecological indicators),能夠幫助他們做環境和漁業的資源管理,讓他們經由指標判斷什麼魚可以抓、什麼魚不行之類的問題。」當時相當流行發明生態指標,至今仍是一門顯學,因為不管是政府單位或研究單位都想找一個簡單可行的標準,因此陸續發展出一百多種生態指標。謝志豪說他當時對漁業一點都不了解,要從不了解到了解,他認真下功夫,遇到不懂就找書唸、找人問。「發明生態指標何其之難,不同的魚受到不同的漁業壓力,要找到一個數值就可以來全面應用,其實我認為不是一個成熟的科學想法。」在大家極力尋找生態指標的情況下,謝志豪卻有相反的想法,「這些指標可能有用,但是它需要和沒有漁撈的狀況作比較,但現實上全世界都是先有漁撈後才去測量這種魚。唯一有用的指標還是回到傳統的漁業管理方法,一個種類、一個種類去做指標,但這不是政府單位想要的,因為已經有研究顯示,單一種類指標有相當大的缺陷。」
因此他提出了一個在當時很創新、奇特的想法,他要比較加州地區受漁撈和沒受漁撈影響的魚種,把受漁撈影響的魚種當實驗組,沒受漁撈影響的魚種當對照組,以此來看漁撈對魚種的影響。這個時候他的實驗室是整個大自然,不受漁撈的魚種受到的環境壓力,單獨來自氣候變遷和生物之間原本的交互作用,但受漁撈的種類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承受撈捕的影響。運用來自約翰老教授的50 年資料,他就能用各式各樣的分析方法來比較這兩種狀況。
「當時我提了這個想法,我的博士班口試委員,漁業界的大老都覺得我是拿橘子和蘋果來比較,根本不可行。」謝志豪打趣地說,每次與口試委員的會議,老師們總是吵成一團,不過因為當時大家做生態指標也做不出個所以然,於是就只能死馬當活馬醫的試試看了。
後來這樣的一篇研究發表到國際知名期刊Nature。即使如此,還是有一些反對的聲浪,但也同時引發了新的研究浪潮。以往的學者曾提出許多相關的物種互動模型,以及魚類族群結構的分析,但往往只停留在模型,沒有以實際的資料去驗證。謝志豪謙虛的說,「我就像走在路上幸運撿到NOAA資料庫的這塊寶,而自己只是從中挖寶。」但若是沒有他一直不斷地進修數學分析、努力鑽研理論生態學,即使有這樣的寶礦在手,也不見得能讓他發光發亮。
成功的研究發表在好的期刊等於博士班順利畢業,這在謝志豪身上卻是不成立的,他發現指導老師希望他能留下來,繼續完成其他研究,加上其他種種壓力,讓師徒二人起了爭執。在崩潰邊緣的謝志豪,很慶幸他的背後一直有一雙支持他的手,讓他不會放棄倒下,這一雙溫暖的手來自他的太太。「我太太一直很支持我,她原本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她選擇放棄工作陪伴我。」說到這裡謝志豪的語氣柔和了許多,透露的是無限的感激與溫暖。
另一方面是前老闆與口試委員們的幫忙,使得杉原教授在最後妥協,也寫了封很好的推薦函,讓他順利在京都大學找到博士後研究的工作。在這段期間他們也迅速將第二篇Nature 的論文送出去,謝志豪說他的老師認為,即使在相處上遇到衝突,但科學研究不應該因為這些事情而受挫折,不繼續前進。即使到現在,謝志豪仍然和杉原教授維持合作,共同指導學生。「我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對我的嚴格要求與挑戰,我自畢業以來,還未遇過比博士班生涯更大的挑戰。」
創建台灣海洋生物資料庫
2007年回到台灣,在台大海洋所開始建立自己實驗室的謝志豪,對於研究走向經過一番思索後,回到了他碩士班時期做的海洋浮游生物生態。以往台灣幾乎沒有完整、且有系統性建立的海洋生物資料庫,研究人員都是到處抓資料分析,能分析的參數有限,空間象度也有限。謝志豪認為這樣不行,「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資料庫,這個資料庫30年之後會有用,將來我能夠像約翰老先生一樣找個good hand來好好利用它」,因此決心要投注心力在創建台灣浮游生態資料庫。這是一條披荊斬棘的路途,箇中艱辛只有實際去做才會瞭解。
「你可以想像我需要花多少時間、多少人力、多少經費,才能完成一個資料點,而一篇論文需要累積4、50個資料點才夠,我需要投資的遠遠超過想像。」這個資料庫中的資料相當齊全,包含海洋環境的背景資料,如溫度、鹽度、溶氧量、各式營養鹽;以及浮游生物的資料,如浮游植物的濃度、生產力、浮游動物的濃度、種類等。
謝志豪這一等就是6、7年,其間慫恿他發表論文的聲音不斷,卻動搖不了他不做「泡麵式」發表的決心,他認為當資料搜集還不夠說一個完整的故事時,連自己都說服不了,怎麼說服別人!

難道就這樣放棄漁業研究了嗎?其實謝志豪並沒有放棄,2008 年發表在Nature期刊上的論文是延續博士班的研究,著重於漁業對魚群豐度的擾動,運用NOAA資料庫的資料分析,發現漁民撈捕時篩選體型較大的魚,造成魚群的年齡金字塔低齡化,進而提高魚群群族崩解的風險,是在對漁業提出沉痛的警告。此外,2012年發表在Science 的研究,則是以加州最著名的鯷魚與沙丁魚漁業為題,探討這兩種族群一增一減變動背後的真正原因。
問到未來有沒有可能回過頭來研究台灣漁業,謝志豪在短暫思索後回答,「我在等一個契機」,這個契機是讓漁業的採樣方法,以及獲得的資料更可信。「我還是想建立一個30 年計畫,期待將來有幫助。當然也有人跟我說,30年之後沒有魚了怎麼辦?那我真的無話可說了。」謝志豪也感嘆,我們對台灣附近的海域了解真的很有限,常常都在處理新的、不了解的現象。以往針對局部、特定種類的調查較多,卻缺乏大規模的調查,在我們還不夠了解自己的海洋的情況下,魚群卻已經面臨慢慢減少的危機。台灣海域面臨的另一問題是,即使規範了台灣的漁民,卻無法規範外國鐵殼船入侵的無奈。
蓄勢待發 航向新大陸
航行於波濤洶湧的大海,如何克服暈船、挺過暴風雨,需要的是不畏艱難的意志力。能夠乘風破浪地前進,航向未知的大陸,需要堅強與堅定。發現新大陸時,要的不只是攻頂插旗,求的是全盤的了解土地。謝志豪的研究之路一如這個旅程,克服困難、險阻的無畏精神與努力不懈的毅力,引領船隊向前挺進。

謝志豪說,當你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就開始努力規劃自己的生活,不做浪費時間的事情,即使你的努力當下看不見,但你從過程中總是會學習到你下一步可能會用到的技能,不管是團隊合作、知識的積累、如何面對新的挑戰等。他從不要求學生要做什麼,反而要他們自己去想、去執行,訓練他們獨立自主研究、邏輯思考和時間安排。
從2013年起,謝志豪與台大大氣系郭鴻基教授合授「生命科學數學」,希望能讓學生物的學生們,瞭解數學的樂趣與應用,開拓更寬廣的視野。我們可以期待的是,在謝志豪老師的帶領下,30年後完成的不僅是一個完整的台灣海洋生態資料庫,更是一批關切海洋生態的專家,在各地發芽茁壯。
延伸閱讀:
走訪明星研究船—海研一號
與一隻臺灣新紀錄海膽的邂逅與聯想
什麼?!你還不知道《科學月刊》,我們46歲囉!
入不惑之年還是可以當個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