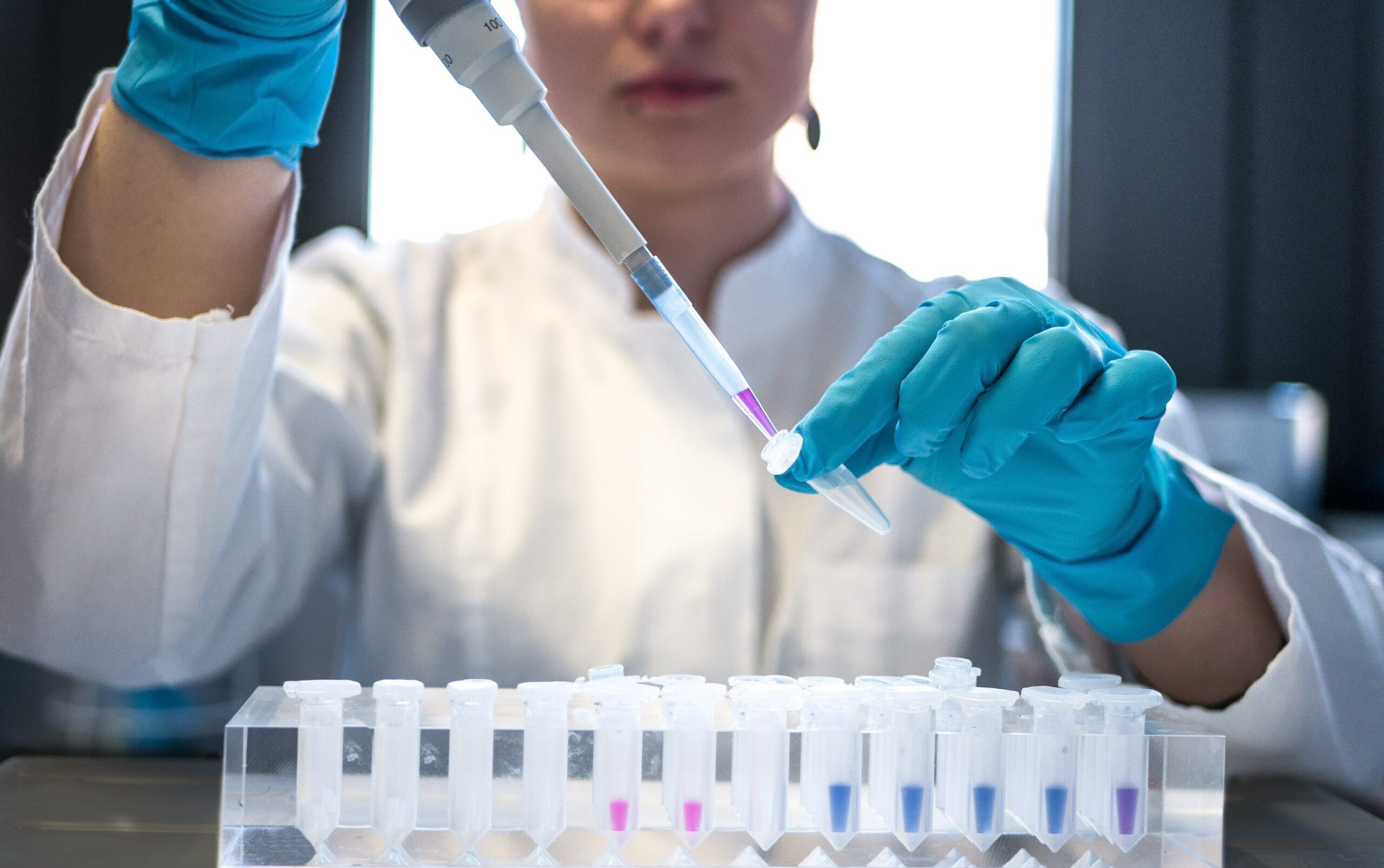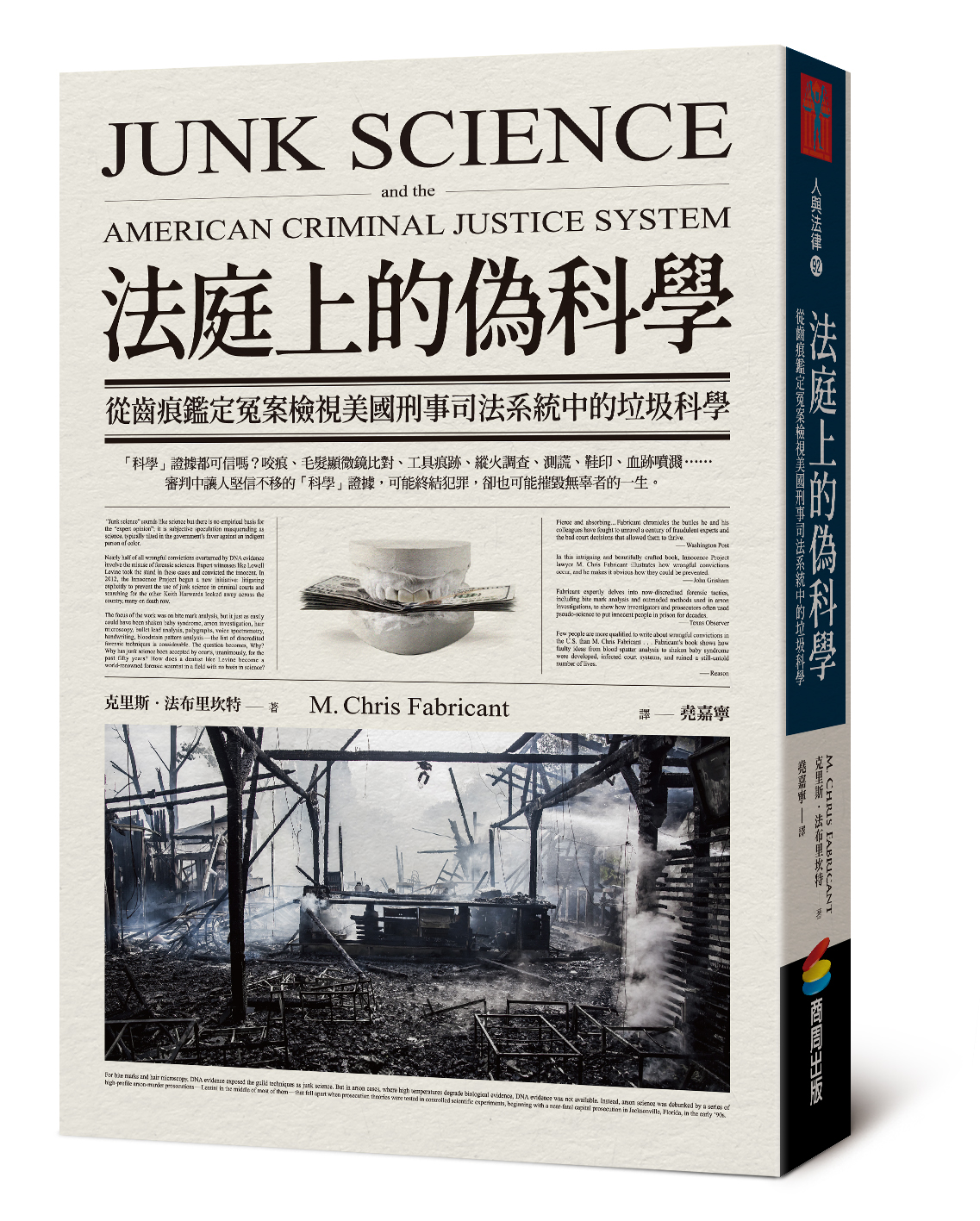撰文:丹尼爾.賽弗特(Daniel Seifert)
最駭人的凶殺案發生時,如何逮到凶手?有時候,單純聞聞屍體或觀察蠅蛆就能伸張正義。跟著《Discovery探索頻道雜誌》深入鑑識科學的領域,檢視線索並思考罪犯如何掩蓋行跡。

一把把彎刀在豔陽四射的高溫下閃耀著。71把鋒利的割稻鐮刀像士兵一般一字排開,這些刀具為71位農夫所有,其中一人砍死了一位同村村民,死者倒臥血泊之中。問題來了:如何找出邪惡的凶手?在沒有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又如何從這71把刀中找出殺人凶器?說不定根本找不出來,因為凶器上的血跡已經被偷偷擦掉了;不過,地方官宋慈知道如何抓出真兇。他靜靜地等待。
71名嫌犯滿身大汗地站著,全都不發一語但個個焦躁不安;烈日下,鐮刀刀面閃耀,接著,微弱的嗡嗡聲出現,聲音愈來愈大,蒼蠅開始往其中一把刀聚集。宋慈笑著指向那把鐮刀的主人:凶手已然現身。金屬刀身上看不見的血跡吸引了饑餓的蒼蠅蜂湧而至,洩露了真相,痛下毒手的農夫終於坦承犯案。
時值西元1235年,中國一處僻靜之地揭開了犯罪史新頁,除了這個故事,宋慈也記錄了許多其他案例,催生了史上第一本鑑識教科書;宋慈就將此書命名為《洗冤集錄》。
屍體會說話
接下來的八個世紀,鑑識學有了長足進展,但仍沿用部分方法,舉例來說,宋慈的昆蟲助手目前依然是謀殺案的破案好幫手,這就是法醫昆蟲學,但可不是光鮮亮麗的學科。蒼蠅需要產卵的地方,腐爛的人類屍體溫暖又黏稠,正是絕佳所在,這是害蟲防治公司奧瑞金(Origin)的執行長卡爾.拜波提斯塔(Carl Baptista)與本刊分享的知識,他自稱蛆蟲達人(Maggot Man)。
拜波提斯塔笑道:「假設我明天死在這裡,沒人移走我的屍體,我開始腐爛,第一天就會有蒼蠅出現。」隨著這尊假想的屍體繼續腐爛,形形色色的昆蟲將在屍體下蛋,拜波提斯塔接著說:「達爾文說,如果兩種物種須在同一個區域競爭,強者將會留下。」
正因如此,鑑識人員才能估算死亡時間——當然無法精確到幾小時,但至少可以知道天數。拜波提斯塔解釋:「估算方法是根據屍體上有哪些昆蟲,以及昆蟲變態(metamorphosis)進行到哪個階段而定。」接著,拜波提斯塔更仔細說明,有些昆蟲只吃壞死的組織,所以會先吐出液化酵素,將組織液化後才開始大飽口福。
來自舊金山的法醫病理學家茱蒂‧梅麗奈克博士(Dr Judy Melinek)與米歇爾(T.J. Mitchell)合著的作品《告訴我,你是怎麼死的》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知道梅麗奈克用哪些工具檢驗屍體後,你看待湯勺的態度將從此不同。
梅麗奈克與本刊分享:「數百年來,解剖病理學的應用並沒太大改變,」她使用的許多工具在一般人的廚房裡都找得到。「我用一把大的主廚刀切開肝臟,片魚刀用來劃開心臟,然後用湯勺將體腔中的液體舀出來。」還有,她也「借助園藝用的高枝剪剪開肋骨,就是那種用來修剪枝葉的長柄剪刀,剪開胸腔後再來處理肺和心臟。」
這工作聽起來不適合膽小的人,此外,驗屍也是體力活;當一天的工作結束,梅麗奈克脫去厚重的塑膠圍裙、護目鏡和泰維克(Tyvek)製造的全身式防護衣,常常已滿身大汗、疲憊不堪。梅麗奈克嚴肅地說:「屍體的重量真的死沉沉。」要好幾個人才有辦法將沉甸甸的屍體搬上搬下推床;「我第一次去犯罪現場時,一位調查員告訴我:『一切就交給地心引力』。」你知道什麼事也很累嗎?小心翼翼地將滑溜溜的器官一個個摘除;梅麗奈克說,尤其是器官異常腫大時更累,而隨著肥胖人口比例激增,看到器官異常腫大案例的機會也愈加頻繁。
梅麗奈克判定死因的方式也出乎意料地原始,《告訴我,你是怎麼死的》一書探討如何運用感覺與聲音;她本人也證實,接受醫學訓練時,不能忽略任何一種感官,因為所有感官知覺都有助法醫判斷。首先,要直接觀察屍體,評估其外形輪廓、顏色、形狀,並搜尋瘀傷或創傷的痕跡,或運用聽力「傾聽斷掉的骨頭喀喀作響的聲音」;如果發現劈砍的傷口,要用手觸摸感覺傷口是否呈現不規則斷面。就連味道也能將死者的一生透露得一清二楚;「聞聞屍體的味道,可以知道死者是否罹患糖尿病,糖尿病病患會散發甜甜的氣味,」梅麗奈克說,「肝衰竭聞起來有霉味,酒精中毒的話,屍體內部聞起來像釀酒廠。」
此外還有「第六感」,梅麗奈克表示,這大概是法醫最重要的特質;第六感就是直覺,如果蒐集到的案情與屍體提供的證據不符,厲害的法醫腦中就會警鈴大作。
等會兒再回來談屍體如何提供各種線索,現在要先認識一下許多人口中的鑑識科學之父。
無處可躲
愛德華‧羅卡(Edward Locard)1910年設立全球第一間警局實驗室,直到1966年逝世前始終是各界公認的法國版福爾摩斯;這個稱號確實名符其實,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調查員至今仍努力實踐羅卡的箴言:「凡接觸必留下痕跡。」知名鑑識科學家保羅‧科克(Paul L. Kirk)對羅卡原理做的闡釋值得一看:
「(罪犯)每踏出一步,摸過或留下任何東西,就算是下意識的行為,也將成為對其不利的無聲證人;除了指紋或足跡,罪犯的毛髮、衣物纖維、打破的玻璃、殘留的工具痕跡、顏料上的刮痕、留下或搜集的血液或精液,以及其他許多痕跡都將構成對其不利的證據。這些證據永遠不會遺忘犯罪事實,不會因當下情況混亂而混淆,也不會因為缺少目擊證人就不存在。這是事實證據,物證不會出錯,不會作偽證,也不可能完全不存在,只有當人類未能找到、研究並了解物證時,物證的價值才會降低。」
由科克的話可以看出,執法者有許多方法可以逮到嫌犯,我們提過法醫昆蟲學,亦即利用昆蟲確認死亡時間,另外還有研究體液的法醫血清學,透過研究花粉與孢子判定死者到過何處的法醫孢粉學,研究毒物的法醫毒物學,專攻手寫筆跡的法醫筆跡學,以及透過牙齒一窺究竟的法醫牙科學。牙齒從年輕的時候就會開始吸收環境中的鉛,世界各地蘊含的鉛同位素含量都不一樣,科學家可由此概略推斷死者來自何處。
羅卡年輕的時候,甚至還有法醫視網膜影像學,使用這種技術的人相信,如果對著屍體的眼睛照相,可以捕捉到死者生前看到的最後一幅影像,令人毛骨悚然。理想的情況下,該幅影像應該會呈現凶手的樣貌;倫敦有位警察還記得這項技術曾用於開膛手傑克的其中一名被害人瑪莉‧珍‧凱莉(Mary Jane Kelly)身上。視網膜影像學聽起來像是偽科學,但至今還是有人從事相關研究。
英國科學家最近進行了活體實驗,透過近距離拍攝眼睛,精確捕捉到受試者注視的影像;研究者指出,從受試者眼中捕捉到的臉部影像,大小為受試者臉部的三萬分之一,即便在某些實驗中受試者不認得「罪犯」的臉,辨識凶手的正確率仍高達71%。
科學家表示,擄人或孩童綁架等案件中,歹徒會幫被害人拍照,這些相片中反射的影像將能幫助警方辨認出歹徒,科學家也警告:「除了身處何處或與誰同行,影像中的眼睛可能會透露出更多的資訊。」一頭栽入未來世代的鑑識技術前,我們先看看一百多年來協助逮捕罪犯的證據:指紋。科學家到現在都還不確定我們為什麼有指紋,有些人說指紋讓我們抓東西抓得更穩,有些人卻不同意。只要碰過某樣東西,就會留下個人的蛛絲馬跡,我們會留下指紋是因為皮膚上有皮脂腺分泌的油質,而油質會與汗腺分泌的體液混合並留下指紋。兩個人留下的指紋完全吻合的機率只有640億分之1,所以指紋在鑑識科學中極富價值,但可惜的是,犯罪現場十個指紋中大概僅一個清楚到能成為證據。
幸好現在各界正不斷開發新技術以採集更多指紋,約翰‧龐德(John Bond)就是其中一人;龐德是萊斯特大學的榮譽院士,同時也是英國北安普敦郡警局的科學支援部主管。龐德開發出一種技術,在子彈射出後還能從彈殼上取得指紋;他寫道:「擦拭彈殼或用熱肥皂水清洗都沒有用,」並不影響指紋辨識。指紋採集的流程是先將槍枝或子彈等金屬裹上一層導電粉再通電。
即便罪犯聰明地洗掉自己的指紋,手指碰觸金屬時還是會造成些微腐蝕,腐蝕處就會吸引導電粉;龐德寫道:「就算高溫使一般的線索蒸發掉了,警方還是可以證明誰曾經使用過某把特定的槍」。如果從頭到尾都帶著手套怎麼辦?你一開槍,子彈擊發後的射擊殘跡(簡稱GSR)就會留在毛細孔與衣物上,這些物證就能證明你與那把槍有關。

掩蓋證據
事實上,如果試圖掩蓋痕跡,可能會因此留下更多線索。舉個好懂的例子,有個以色列的竊賊想要簡單破門行竊,他自以為聰明地脫掉鞋襪,把襪子套在手上,心想這樣一來就不會留下指紋,沒錯吧?結果警察卻注意到別的線索:赤腳的竊賊依稀留下了足以將其定罪的足跡。這個經驗老道的小偷沒想到,足跡、掌紋跟指紋一樣,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執法機關表示,越來越多罪犯會掩蓋自己留下的痕跡,這可說是《CSI犯罪現場》這類熱門犯罪影集造成的。漂白水會破壞DNA,所以現在犯罪現場常發現漂白水被兇手用來掩蓋蹤跡;此外,罪犯不但常戴手套,也學會用膠帶封住信封,而不再像以前那樣用舌頭舔封口而留下大量的DNA證據。
新加坡鑑識專家團隊的資深顧問鑑識科學家林貞貞坦承,「罪犯的確多少會學習,然後試著掩蓋痕跡,」但不可能掩蓋一切;林貞貞與本刊分享道,「有時當你試圖掩蓋蹤跡,反而會在無意間留下其他的證據,」她微笑說道,這就是羅卡的交換原理。林貞貞的同事鄭明龔博士(Dr Michael Tay Ming Kiong,音譯)也相當贊同,還舉了新加坡當地一宗駭人案件「碎屍案」(The Body Parts Case)為例,該案中的犯案男子便將愛人剁成碎塊。
「將屍體剁成碎塊之後,他用報紙和塑膠袋將屍塊包起來,再用腳踏車載往棄屍地點。」從多處棄屍地點與犯罪現場找到的微量跡證幫助鑑識科學家指出嫌犯與案件的關聯,並且重建了可能的事件先後順序。
「警察來到他家,雖然他曾試圖清理,但現場殘留許多證據,」林貞貞補充,「現場還有掩蓋的跡象,這對嫌犯來說更糟,因為這樣他就不能說:『喔,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群亞洲鑑識專家執業數十年來,見證了科技如何變得更輕巧且易於攜帶,這代表鑑識人員可以現場檢驗證據,並且快速將調查線索與情資傳給調查員;工具也變得更加精密準確,可以採集或檢驗極微量的DNA、可燃液體、不知名化學物質或其他遺留在現場的物品。林貞貞最喜歡的鑑識小知識是什麼呢?一丁點大的車用顏料就足以回溯找到車子的品牌與車型。
林貞貞的同事謝寶玲(Chia Poh Ling,音譯)表示,小到細胞層級的精準度也有其問題,誤判陽性反應就是一例;「在我們的環境中,許多物品都以石油產品製成,」日常生活中會使用到的東西幾乎都是如此,諸如地毯、維他命膠囊、塑膠、光碟與義肢,所以如果能測出微量的石油,很可能只是其他物質的干擾,而不是發現了具備殺傷力的汽油彈等物品。謝寶玲說:「之前有個案子,我們在一件衣服上偵測出非常微量的石油,」就連某些人造纖維也可能有些微的石油含量,「所以,如果在某個地方發現炸藥,而該處先前曾是戰地,那炸藥是戰爭留下的?或是某個恐怖組織最近留下的?」
不過,科技仍會不斷進步。梅麗奈克博士表示:「最新的個人DNA鑑定技術能幫助我們找出正確的嫌犯,」她接著提醒,「但這只是個有效的工具,也就是達成目標的方法之一。」
「DNA鑑定並不能取代嚴謹的警方工作與驗屍程序;如果沒有經由正確的方法蒐集、記錄,DNA鑑定的結果也無法成為呈堂證供。此外,如果鑑定指出的對象本來就會留下DNA,例如配偶或家中成員,那也證明不了什麼,不代表那個人就是兇手。」林貞貞說,到頭來科技其實對檢方與被告都有幫助。
就以偽造為例:這些鑑識專家曾經檢視過真的與假的勃起障礙藥物的包裝。拜高科技印刷工具所賜,現在愈來愈難以肉眼區分真假,有時候「假藥的包裝其實印得還更清楚。」
就算沒有科技幫助,還是會受到CSI效應的影響;此效應取自2000年首播的電視影集,還衍生出一堆外傳與模仿劇集。CSI影集中的主角不是嚴肅沉悶的科學家或探員,而是年輕時髦又精通科技的科學家,利用狡猾但粗心的凶手遺留在犯案現場的毛髮或血漬破案。
影集大受歡迎的結果導致陪審團現在每每希望檢方能提出DNA證據,若缺少DNA證據,陪審團判決有罪的機率就較低。一項2008年的研究顯示,69%的美國法官認為陪審員對鑑識證據的期待不切實際,有些案件的罪犯甚至因此無罪釋放。
就算提出的鑑識證據毫無破綻,到最後,定罪與否還是掌握在人類的手中,這也就牽涉到心理學了。2011年一項研究顯示,法官吃過午餐之後,比較容易讓犯人假釋出獄;在實驗室數百個小時的努力,求的是罪犯終生監禁,難道最後就因為法官在判決前吃了大麥克而功虧一簣嗎?研究發現結果就是如此。其他研究則顯示,外貌姣好的被告比相貌平庸者更容易獲判無罪。

不過是凡人而已
我們和鑑識專家的談天以大哉問收尾:我們愈來愈了解各種證據,會不會有一天再也沒有凶殺案件?當哪天連被害人的眼球都能做為證據,罪犯會不會認為自己無論如何都無法逃過法網?鄭明龔的答案是肯定的,嗯……其實是部份肯定,「我想,不管鑑識科學如何進步、逮住凶手的準確率有多高,還是有人會衝動犯案;在沖昏頭的當下,就算知道這是錯的,甚至可能因此被判死刑,有些人還是會照做不誤。」
這是人類本性令人灰心的一面,也帶出了我們的最後一個問題:多年來沉浸在證明人類惡行的可怕證據之中,對人類有沒有什麼新的體悟?謝寶玲稍稍停頓之後,給了我們九個字的回答:「任何人都可能會殺人。」顯然,八百年多前,中國古代的調查員宋慈盯著那些農民與成堆的割稻鐮刀時,心中所想也是如此。
本文出自《探索頻道雜誌國際中文版》2015年07月號第30期



























《運動基因》立體封面72dpi.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