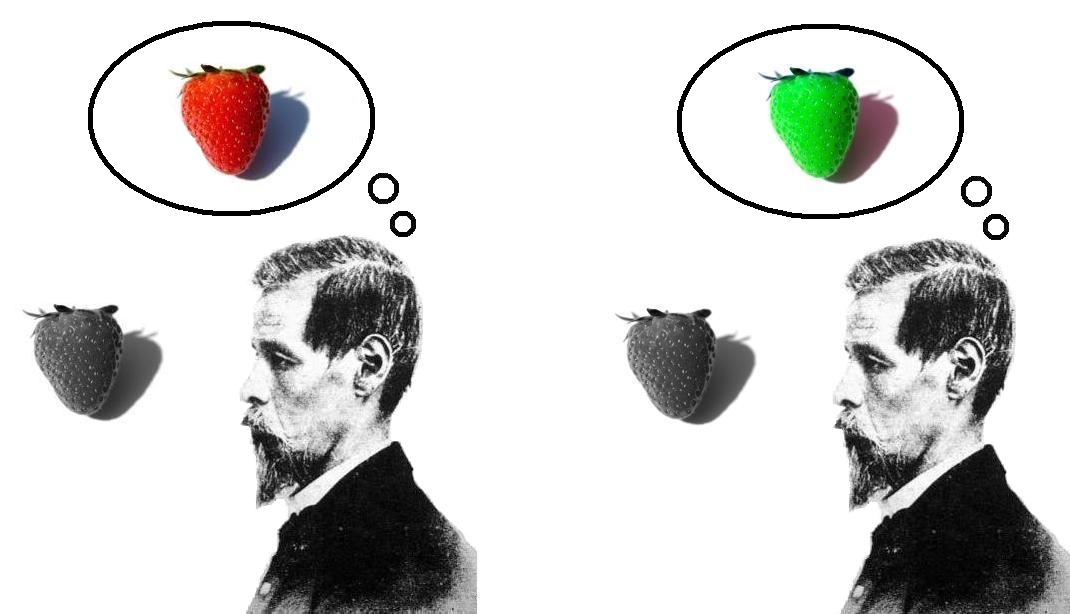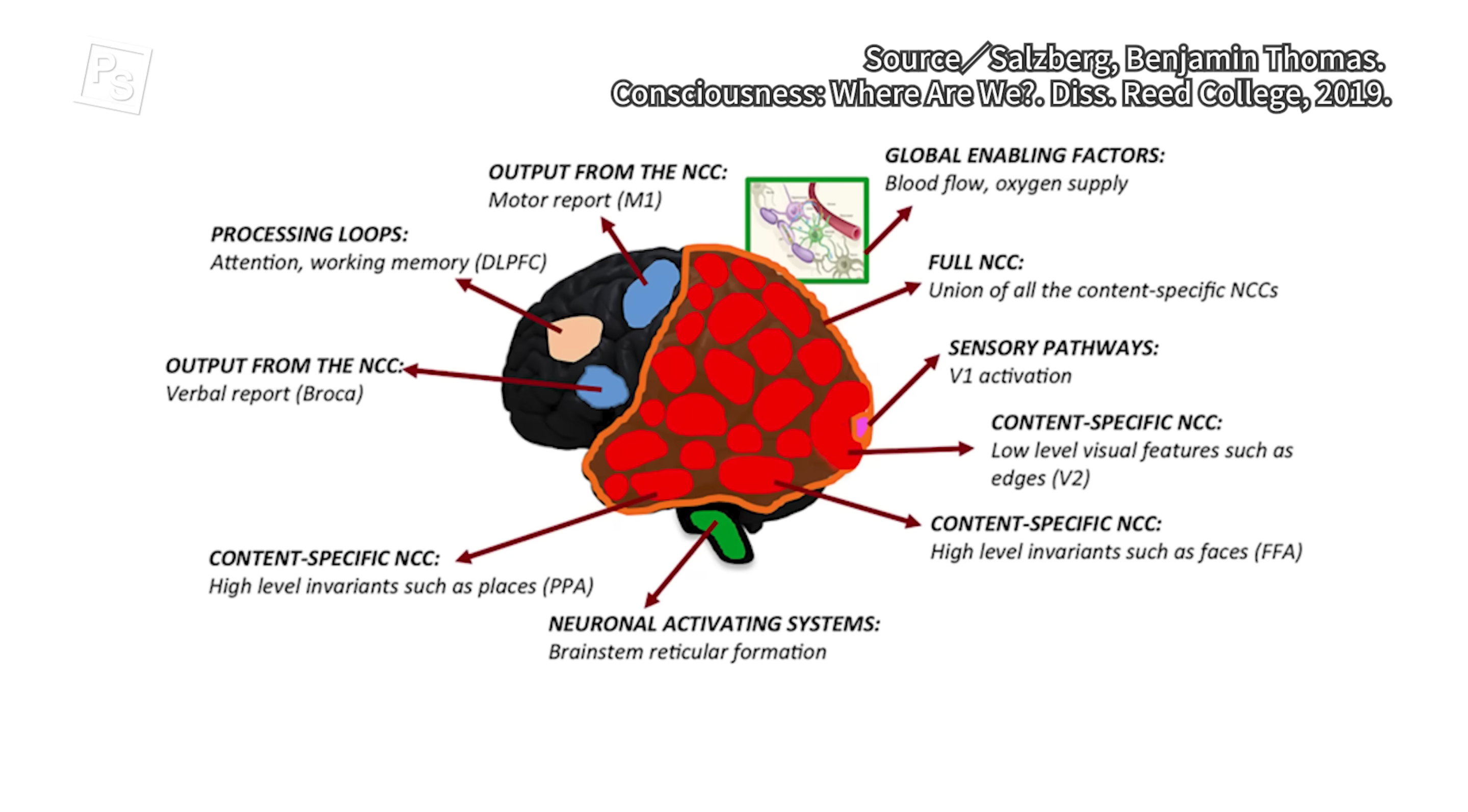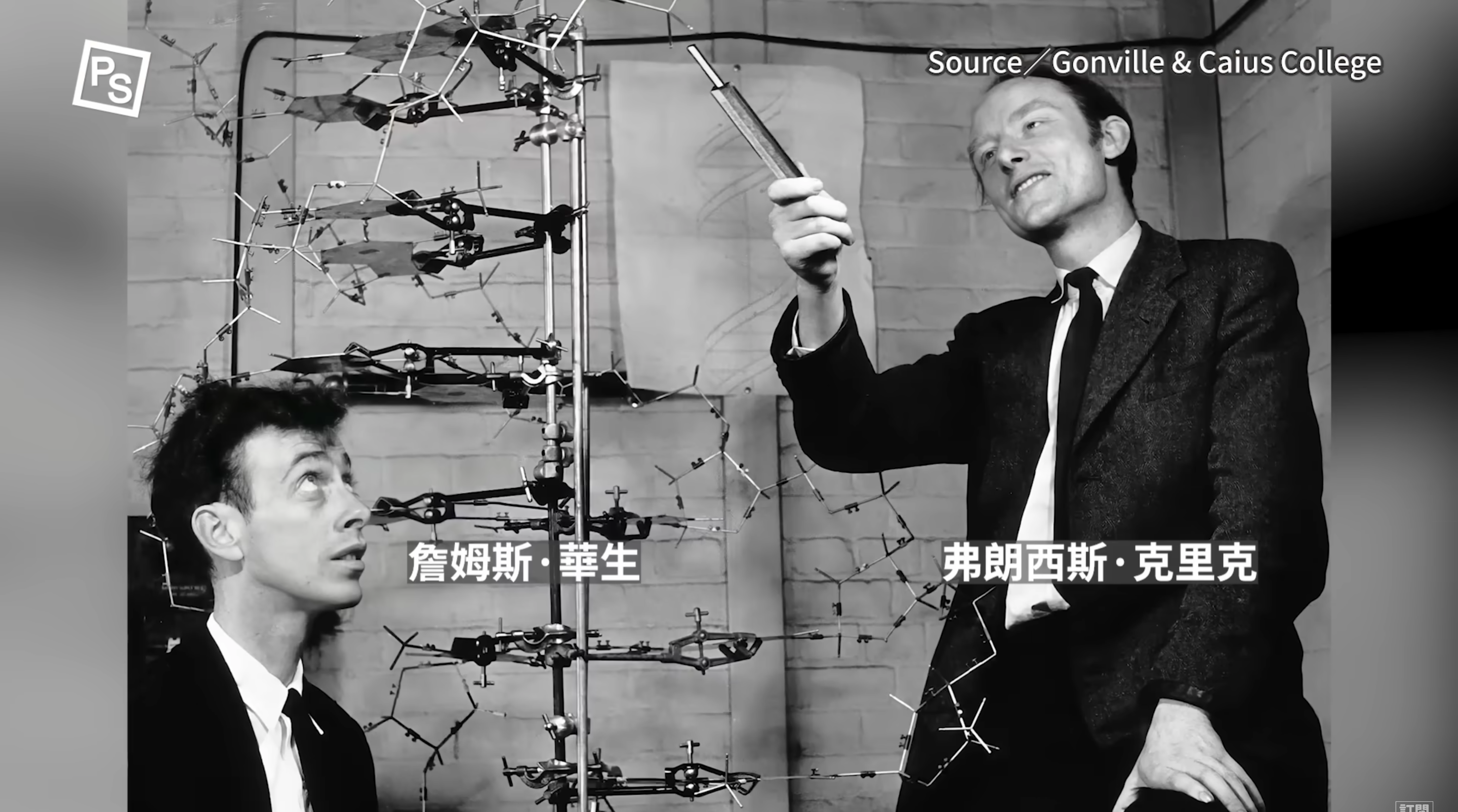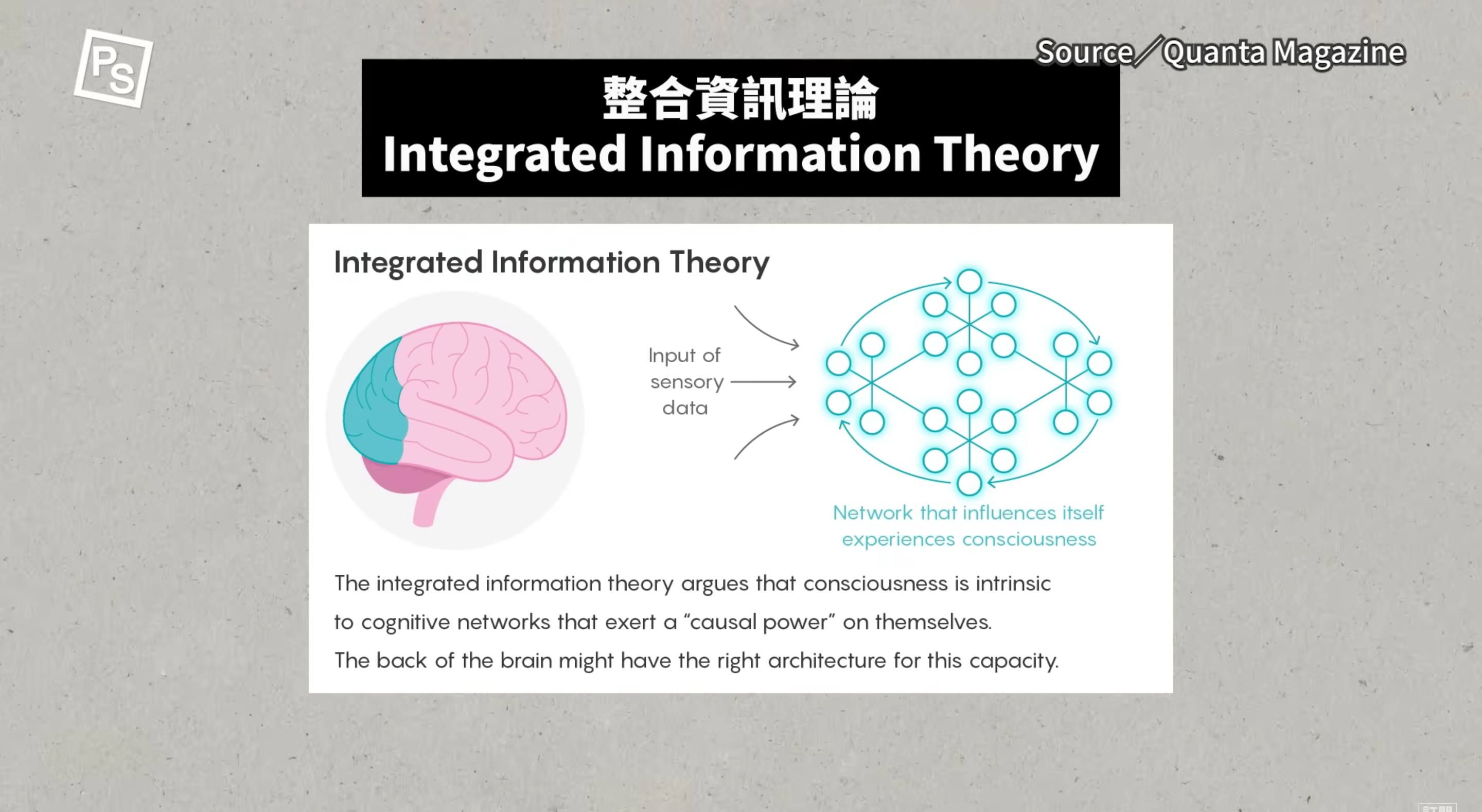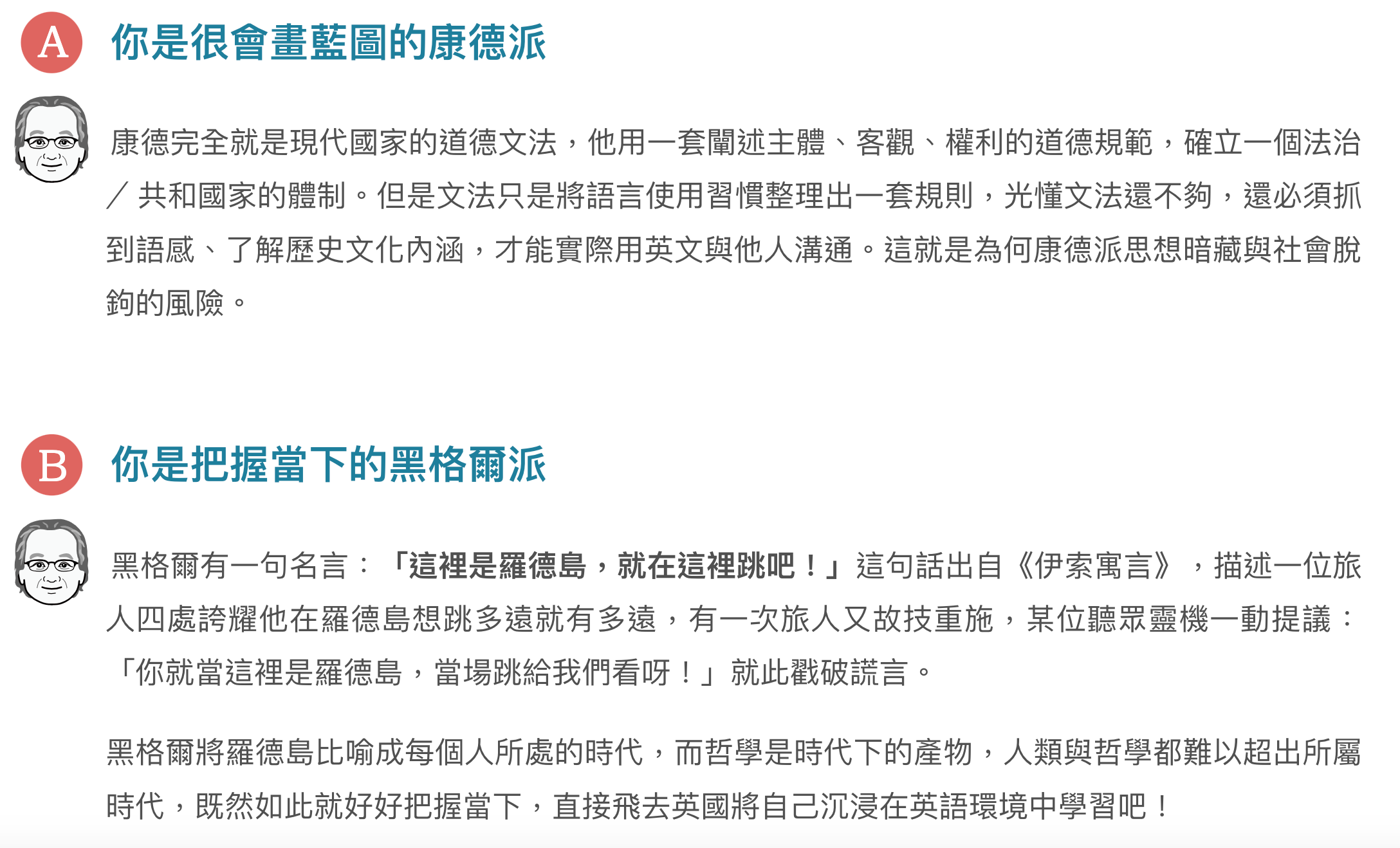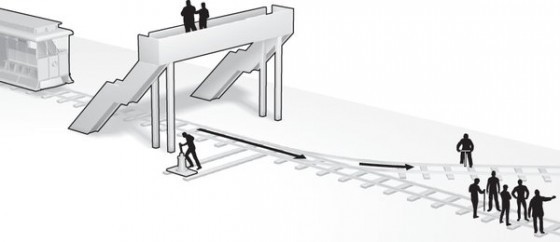
文 / Wenson
泛科學這兩天登了一篇文章,轉載和討論的人不少,標題是〈舉世爭議的「電車難題」是戲弄人的詭辯〉,方才看了以後認為其中大有問題,也在文章裡留了言。我不喜歡打筆仗,因此這裡絕少會針對單一文章寫篇東西來反駁,不過轉念想想,這倒也算是個不錯的引子,可以談談某些對於哲學常見的誤解。
這兩三年,「哲學」在台灣的網路討論裡佔據了前所未有的份量。隨著社群網站上的公眾議題討論風氣,論理清晰簡明、不需要太多知識背景的分析哲學也就跟著冒出頭來,再加上主要推廣者本身的專長與偏好也是分析哲學的比例比較高(外加Sandel這個暢銷書哲學家助拳),整個扭轉了情勢,從前名字最常被提起的哲學家多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等人,現在好像更常看到Rawls、Sandel、Dworkin、Chomsky、 Popper、Kuhn這些人的名字。當然這種現象也有時代或世代本身的因素,願意搬起大部頭慢慢啃的人變少了,就像前陣子聽李明輝教授說的,20年前開康德的課會爆滿到大家要排隊搶著聽,現在開康德則是能湊滿開課人數下限就算不錯了。在我們的時代,大眾心中的哲學多多少少有了「典範轉移」,而且看起來這勢頭才剛開始,不知還要走多遠。
然而,就算是身價看漲的分析哲學,似乎依然無法擺脫宿命,即使高端大氣上檔次了,勢頭走紅看俏了,願意花功夫深究的還是少數,我這不是在批評什麼,因為其 實放眼歐美也差不多是如此,願意給予「哲學」多一點的關注,已然殊非易事(至於哲學值不值得這樣的地位或尊號,那是另一個問題)。上頭提到的泛科學那篇文 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者根本就誤解了思想實驗的目的。
哲學家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就是不斷思維,思考各種天馬行空的可能性,而「思想實驗」就是哲學家幾千年來常用的方式。由於這些設想通常都很曲折或詭異,所以也格外容易引起人們的興趣與好奇心,正因為這樣,所以市面上的哲普書或推廣講座裡常會提起一些思想實驗,有的更已經成為不少人都聽過或甚至都可以 說個一兩句的著名「案例」,例如桶中腦、孿生地球、Gettier Problem、黑白瑪麗、中文房間等等。的確,這些思想實驗本身都妙趣恆生,甚至像極了腦筋急轉彎,大大有助於提起大家對於(分析)哲學的興趣。然而, 西方哲學是一個提問題的學問,而且是一個問題串著一個問題,也可以用一個問題打倒另一個答案,思想實驗作為一種哲學工具也是如此,如果把它當成是有正確解答的腦力競賽,以為只是詭辯家的話術,恐怕是混淆了目的與手段,甚至是買櫝還珠。
的確歷史上是有詭辯家的,但是思想實驗不是辯論比賽,設計這些實驗的人不是要創造一個解不開的難題,然後告訴大家「看啊你們這些人都被我難倒了吧」,分析哲學尤其不是如此。絕大多數的思想實驗,包括前一段提過的那幾個,都是用來推翻一個常見或既定的(哲學)觀點,用來證明原本的理論有所不足,所以一定要跟它想挑戰的對象一起看。以電車問題來看,創始人Phillipa Foot想要攻擊的對象是效益主義,所以問題不在於到底應該撞死五個還是一個,而是「我們不見得會用數字的計算來評判什麼算是比較有道德的」,後來 Sandel在哈佛課堂上舉這個例子(以及後來的胖子)也大致上是跟著Foot的想法在走,他想問學生的是「正義會不會沒辦法用某某標準的效益來算」。如果我們要說Foot或Sandel是在詭辯,那麼應該提出的論點是「為什麼這種設定裡效益主義依然站得住腳」,而不是像該篇文章所說的,「涉及生命數量極 少的道德抉擇,除了具體的道德情境外,也必須了解生命對象的內容進行道德判斷,假如我們對對象一無所知,不過就是抉擇『ABCDEF君』的生死,變成了抽象的數字遊戲,毫無『兩難』可言。」
為了把這種思想實驗的目的講得更清楚,我想援引我以前在〈分析哲學的科學性格〉裡寫過的文字:
科學理論的要旨之一,就是法則要有嚴格性和普遍性,
反向來說,就是要能禁得住各種反例的考驗;以前面講過的牛頓力學的例子來說,
一開始牛頓力學剛推出時,物理學家們利用這套法則來計算各種現象都得到了沒有差錯的結果,
甚至還可以利用這套力學公式,直接預測在太陽系的何處還有第九顆行星存在,
但當我們擁有越來越多的天文和物理知識之後,牛頓的力學卻沒有辦法繼續「對」下去了,
因此,相對論、量子力學一個個出現,取代了牛頓力學,甚至快要「證偽」了牛頓。
順著這套方法,在分析哲學中,舉一個好例子的功效也可以等同於在「舉反例」,
只要能利用該例子來證明某個理論的不足或不完備,那麼自然也就可以「獲勝」了。
我寫文章時總希望盡量少使用術語,而我當初所講的「例子」其實就是在說思想實驗。作為一種「實驗」,如果你把實驗的目的抽離,只看實驗的過程,那是完全沒有辦法談這個實驗到底成功還是失敗的。當然,哲學家不能也不該禁止他人把這些思想實驗拿去引申為其他用途,人人都有發想的自由,但是當有人說這思想實驗是詭辯,甚至破解了這個詭辯的時候,我卻替分析哲學感到無奈,明明好像受捧了,卻又被重重一摔。
其實,思想實驗也不完全只能用來打倒什麼,有的時候也可以用來建立什麼,最好的例子當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無知之幕」。同樣地,這種設定也要依據它的目的來進行討論,如果只是說「唬爛啦,現實世界裡哪有這種情況」,並不能算是有意義的批評,就像我們也可以用簡單一句「哪來的孿生地球和XYZ,你去找給我看看 啊」來反駁Putnam,但那並不會有損於Putnam的哲學意義,只是代表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哲學是在幹嘛而已。
原本想再多講些「哲學的無奈」的,不過又恐變成了學院派的嘮叨,這陣子有很多關於哲學與哲學推廣的東西想談,也許下次再說吧。
原發表於Wenson的隨筆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