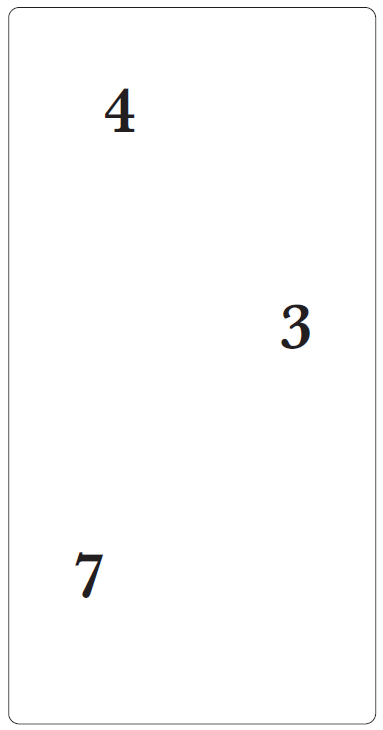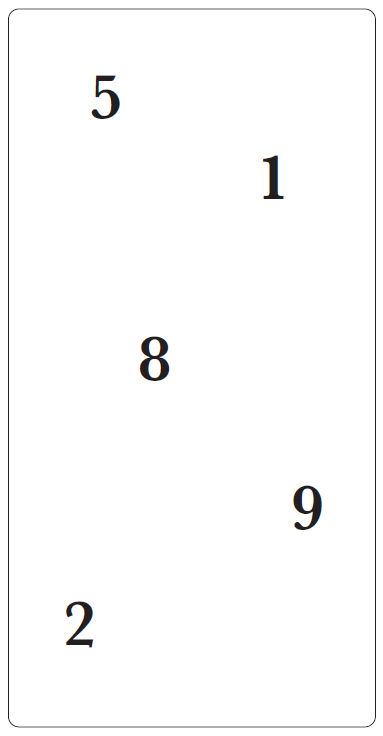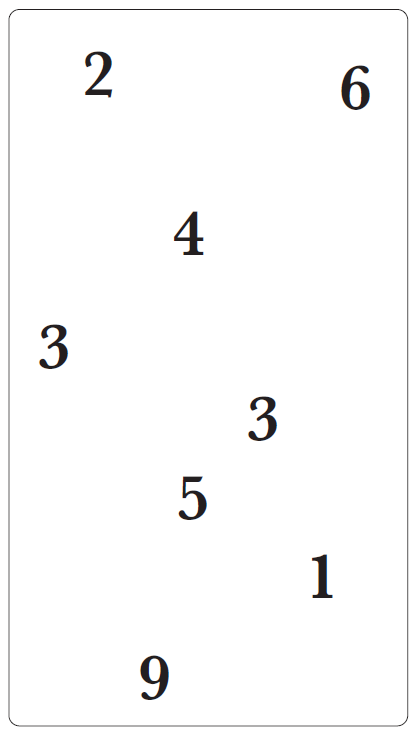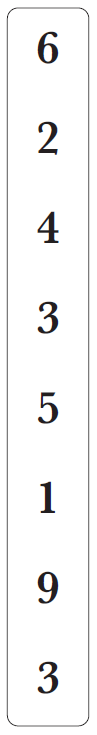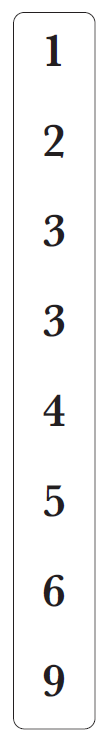- 作者 / 艾佛瑞德 S. 波薩曼提爾、蓋瑞.柯斯、丹妮耶爾.索羅.維葛達默、凱瑟琳.基芙—柯柏曼
- 譯者 / 謝雯伃
我們大多數人都已接受古諺語所說的,習得一項技巧或取得新資訊的最佳方式是透過經驗。如果你想擅長解題,就盡可能多解各種不同類型的題目吧。練習,練習,練習!
然而,這沒那麼容易。
重覆累積不成功的經驗可能會增加挫敗感。預期失敗則增加了焦慮。要從經驗中獲益需要某些指導。

被馬踢到頭而獲得的超能力
偉大的阿根廷作家波赫士寫過一個傑出的短篇故事《博聞強記的富內斯》(Funes the Memorious ),該故事講的是一個住在巴拉圭的年輕人,因為被馬踢到頭而獲得了記住特定經驗的神奇能力:
他心底知道 1882 年 4 月 30 日破曉時分南邊雲朵的形狀,他能在記憶中將這些雲朵與他記憶中儘管只讀過一次的西班牙語著作中色彩斑駁的條紋相比較⋯⋯這些記憶並不是簡單的記憶⋯⋯每一個視覺意象都與肌肉感官、熱感感官等能重建他夢境的感受相連⋯⋯有兩三次他把一整天都重建出來了;他從未遲疑,但每一次的重建都需要一整天。
波赫士的故事到不久之前都被認為是一種幻想。但在 2006 年,研究者出版了一份他們稱為 AJ 的病人之案例研究。
AJ 與故事中的 Funes 有許多共同處,她能記得每一件自己所經歷過的事;她吃過的每一餐的每一個微小細節,以及她經歷的每一次社交互動。她解釋說:
我現在三十四歲,從我十一歲起,我就有這種能回憶過去的神奇能力,不是只有回憶而已⋯⋯我可以從 1974 年起直到今日的每一天中隨便選個日期,然後告訴你那天星期幾,我那天做了什麼事,又那天是否有任何重要事情發生⋯⋯只要我看到電視上閃過一個日期(或在任何一處看見某個日期),我就會自動回到那天,記得當天我在哪裡、在做什麼、那天星期幾之類的。
稀少的存在——超憶症能記得生活大小事
這個情況被稱為超憶症,或是超常自傳式記憶。這個情況極為稀少,僅有幾個人身上出現過。
AJ 的能力似乎很神奇,某種程度上可與電腦的能力相比擬——就像隨身碟,大概只有一包口香糖大小,卻能裝下幾乎兩百萬份文件、兩百首歌曲以及三十萬張相片。
但是,如果記住過去經驗如此重要,為什麼超憶症如此稀少?為什麼並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相似的能力?研究顯示,我們大多數人對於過去的記憶記得很少,也常常扭曲記憶。
答案是,我們心智設定的目的並不是記錄經驗過的一切確切細節。演化把我們的心智設計為解決特定問題,而記憶眾多細節並無法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波赫士暸解這點,於是他記下 Funes 自己的看法:「我一個人擁有的記憶比世界之所以成為世界以來所有人類的記憶還要多⋯⋯我的記憶呀,先生,就像個垃圾堆。」AJ 也描述她的超憶症經驗是個可怕的經驗:
它從未停止、無法控制、非常耗神。有些人稱我是個人型日曆,其他人則聽到就嚇得跑出房外,得知我有這項「天賦異稟」的每個人都有的反應是驚愕不已。
接著,他們開始拋給我各個日期,試著要考倒我⋯⋯ 我還沒被考倒過。大多數人說這是一個禮物,但我把它稱為一種負擔。我每天都在腦中重播我的整個人生, 這要把我搞瘋了 !

AJ 並不是唯一一個受此情況所苦的人。2013 年,公共廣播電台 (NPR) 報導了一名被診斷為超憶症的五十五歲人士,他就一直深受憂鬱症所苦。
難不倒人類的臉部辨識
說明我們心智如何運作的另一個範例,是我們辨識臉部的能力。雖然臉部辨認在資訊處理上是項特別困難的問題,人類卻極為擅長解決這類問題。
回到 1966 年,當時普遍認為我們擁有一種「祖母細胞」,它是一種能表徵複雜但特定概念或物件的神經元;當一個人看見、聽見或是敏感地辨別出一個與他祖母臉部相似的特定實體時,該神經元就會啟動。
然而,大多數的臉部揀選細胞並非祖母細胞,因為它們並不表徵一個特定知覺;也就是說,它們不會只針對特定面孔而啟動,不管這張臉的大小、方向及顏色怎麼變化都有辦法辨識。
就算是最具揀選能力的臉部細胞,都有可能錯過特定臉孔,更別說相似度更低的臉孔。
然而,人們卻能區別出數千張稍有不同的臉,更有甚者,我們得在許多不同情況下辨認出同一張臉孔。每一次我們看到一張臉,它在我們視野中都呈現不同角度,在不同光線、地點、化妝或陰影下也有些微不同。因此,如果我們以一個特定神經元的確切感官經驗來辨認臉孔,我們就會慘遭失敗。
事實上,每一次的觀看,我們都必須找出一張臉的深層屬性,而非單單記下某張特定的臉部影像。這讓我們能夠從眾多臉孔中區別出一個人的臉。不同特徵的相對位置是臉部感知的重要面向。我們似乎可以提取兩眼距離或是嘴巴、鼻子和眼睛相關位置等微小差異。
臉部辨識這種複雜技巧,端賴我們在辨認一張臉孔時,是否能從進入我們感官的資訊洪水中提取更深入的抽象資訊。
除了單單記錄任一場景的光線、聲音及氣味,我們還必須回應這個世界深層的抽象特性。這讓我們在各種情況下偵測到細微且複雜的相似性及差異性,而能有效地行動。甚至在我們之前從未遭遇過的新情況中亦是如此。

抽象資訊之所以有幫助,是因為它能指引我們從一堆複雜的可能性中選出我們感興趣的資訊。在臉部辨識中是如此,其他知覺經驗上也是如此。
舉例來說,我們利用抽象資訊來辨識熟悉旋律。一旦你聽過布拉姆斯的搖籃曲,無論它被轉成哪種調或是使用哪種樂器演奏,甚至演奏中出了幾個差錯,你都可以認出這首曲子。
讓我們辨認識出熟悉曲調的不管是什麼,都絕不是你過去聽到這個曲調時的特定經驗記憶。這肯定是出於某種抽象的東西。儘管我們根本沒注意到,但我們總是在辨識行動中仰賴這種抽象的資訊。
波赫士理解到,記住每一件事正好與我們心智最擅長的工作——從一堆經驗中提取資訊——相衝突。這是何以 Funes 將自己的心智描述成一個「垃圾堆」,因為那裡面充滿了無法被歸納或理解的特定細節。他不能理解他多次遇到有四條腿的毛絨絨生物,實際上只是遇上了同一種動物:
「我們不要忘記,他幾乎無法以一種概括且柏拉圖式的方式來處理概念。對他來說,不光理解狗這個概念包含了不同大小及形狀的個體很困難;在 3:14 看到的狗(從側面看)與他在 3:15 看到的狗(從前面看)是一樣的,這件事也困擾著他。」
不用記太多!超憶症反而阻礙我們的專心
我們大多數人並非超憶者,這是因為超憶會讓我們在演化時無法成功做該做的事。我們的心智忙著從我們的經驗中選出最實用的資訊並將其餘拋諸腦後,是為了讓行動有所依歸。
若把每一件事都記住,可能會阻礙我們專心在更深入的抽象準則上,那有助於我們辨識新情況與過去情況的相似處,並找出有效的行為。
行動時要有效率,細節反而非必要;一般來說,我們只需一個大致印象就夠了。有時候儲存細節反而適得其反, 就像超憶症患者及那個記憶如同充滿細節的垃圾堆的 Funes the Memorious 一般。然而在解題時,記住重要資訊對我們來說是有幫助的;有時我們的記憶可能停留在一個我們不想記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