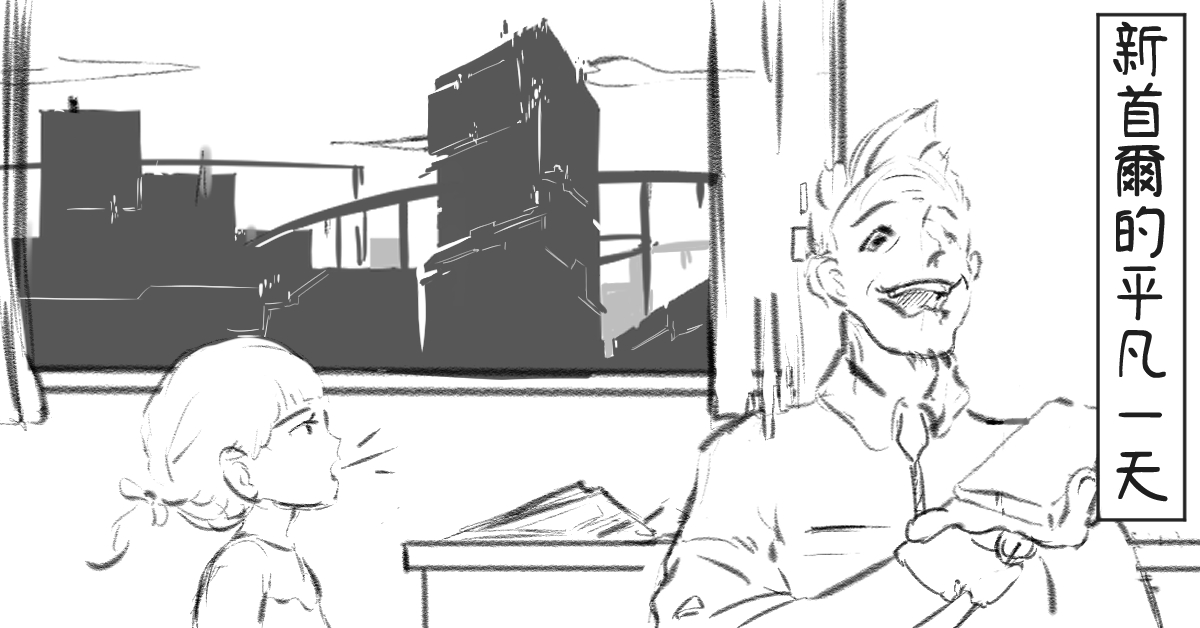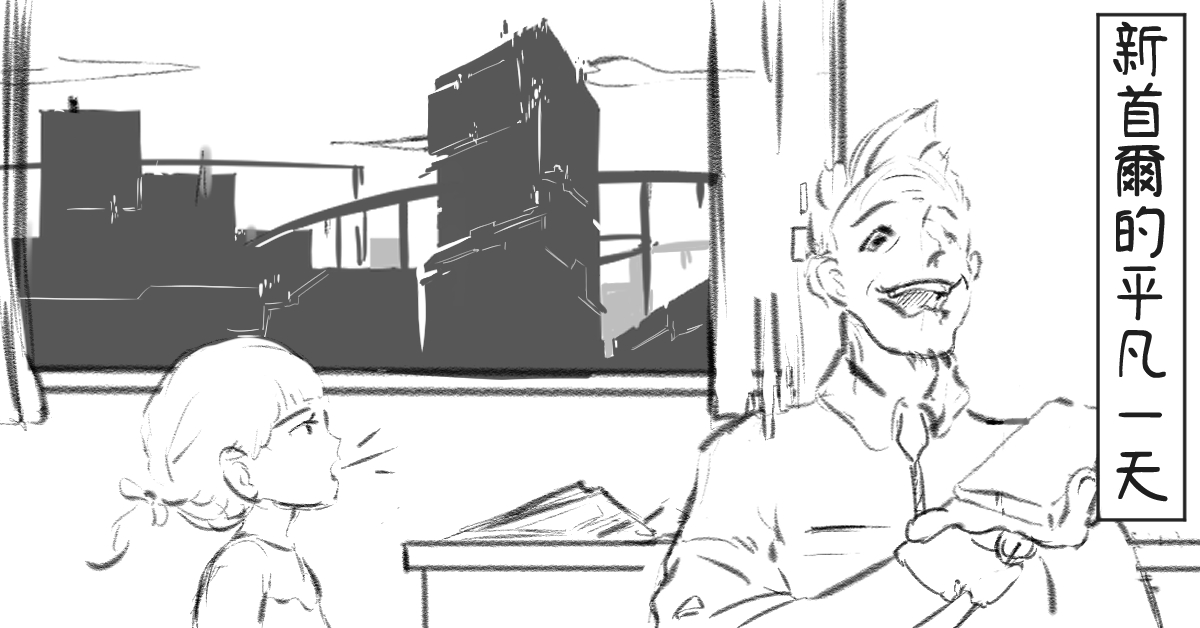A 編按:每周一、三、五晚上九點,泛科學將連載第二屆泛科幻獎的得獎作品!由於每篇得獎作品都是超過萬字以上的中篇小說,為了方便閱讀,我們把每一部作品拆成三個章節分別上傳,預計每週能看到一篇完整的得獎作品!
不想錯過連載?請密切鎖定泛科幻獎!如果想看前面的章節,可以點選標籤中的篇名,或是直接進入泛科幻獎帳號搜尋。

- 作者/蔡旻君
趁著妻子沒注意,羅伊將手掌伸進燃燒的火堆之中,溫暖而非燒灼的感覺再一次證明了他活在虛擬的世界裡。火焰頂上吊著一口已經泛舊的白鐵鍋,那是妻子從老家離開和他同居時一起帶過來的。
羅伊盯著白鐵鍋下緩慢竄起的零星飛火,想著鍋壁左邊這道凹痕是他們倆哪次晚餐後不小心碰傷,鍋底的一塊燒焦又是燉哪一道菜時所留下。他想了很多,多到自己都記不住哪些是想像出來的而哪些又是真實,接著想起他和妻子其實沒有結婚,只能算是未婚夫妻。
一直都是。
妻子從保溫袋裡取出今早醃下檸檬和醬油的鮭魚,將砧板小心翼翼地放上膝蓋後一匙一匙用叉子把魚肉切碎。十一月山裡的涼意比羅伊印象中更加和煦,散發出一股夏夜裡坐在草坪上才聞得到的泥土味道。白煙順著水泥屋低矮的鐵皮遮雨簷向上流進森林,彷彿中和了整個夜晚的黑色。
妻子端著砧板站起來,鮭魚、事先切成花的蔥白、豆腐、用指甲掐斷的豆芽以及柴魚片依次落進滾沸的水中。然後滿意地笑了,轉頭看像山腳下城市閃著燈火的地方。即使入夜,機械人型依然可以不眠不休地繼續進行修築作業,建造到一半的防護牆在月光和無數枚一千五百瓦工程用照明燈的照射下,像顆下半身埋在地底、上半身破了口的蛋殼。瀅瀅散著淡藍色的光。
「蓋好以後,就不能像這樣常常出來了吧?」妻子把眼神移回湯鍋上,攪動時鍋壁和湯杓之間傳來沉重的碰撞聲,聽著讓人不安。「要不要來打賭什麼時候會完工?」
「好。」羅伊回答。同樣的場景、同樣的問題他已經經歷過好幾次,回答「好」是相較之下會讓他心情比較舒坦的選擇。雖然他知道正確的答案,仔細考慮之後還是說了「大概要五到七年吧?」這種模糊沒意義的話。
「要這麼久嗎?我想大概兩三年就會完工了。」
妻子的猜測並沒有錯。防護牆完工後部分建築資料向媒體公開,整體工程規劃約為十年,從現在的比例來看的確只要再兩三年內就可以竣工。但計畫是計畫,人性是人性。在多方商業利益以及環境、人倫團體的衝突與角力之下,竹水城防護牆最終歷時二十一年又七個月、於一個下著汙濁雨水看不見天空顏色的早晨完工。
所以正確答案應該是還要十三年半。羅伊心想。但眼下此刻他只願意把心思放在妻子為這趟登山旅行精心準備的山飯味噌湯。空氣汙染、環境破壞什麼的都先拋在腦後,至少現在他盤腿坐著的這片森林裡還有活生生的樹、樹上有葉,葉子尖梢的露水含有月亮散射的光。
羅伊和妻子偶爾會登山一次,每次喝湯時他都會忍不住落淚。然後妻子會笑他,接著又有些擔心地問他怎麼了。
水泥屋前的山徑朝著城市相反的方向蜿蜒而去,盡頭是一間破敗的小教堂,教堂立在懸崖之上,入夜後可以聽見細微潮騷與鐘的共鳴。
*
「為您播報下一則新聞:昨日由神性合一聯盟於中央大道上舉行的反〈VR法〉集會大遊行,主辦方宣稱共有十萬人走上街頭。神性合一聯盟表示該法案會嚴重迫害下一代人的心靈與思想,人類的靈魂會乾涸。與此同時……」
每天都是同樣的早晨,烏頭翁罕見地露臉在窗外花圃啄食。妻子關掉電磁爐,將邊緣煎到焦脆的培根鋪在蛋和土司上。「羅伊——」
烏頭翁啪咑一下振翅飛走,和羅伊的開門聲正好重疊在一起。他朝妻子走去,接過對方手中的咖啡杯後擱到桌上,然後牽起她的手。妻子饒有默契地轉了一圈,笑著沒有說話。等羅伊也坐好以後將雙手靜靜地在胸前貼合,就像是在祈禱那樣。羅伊已經習慣妻子的這種行為,也明白她沒有所謂的宗教信仰,這個舉動只是單純地表達感謝而已。
「感謝這個世界,感謝眼前的食物,也感謝我的父母。」羅伊和妻子第一次約會時,他問了她這個雙手合十的含意,妻子毫不隱瞞的態度讓羅伊心中產生一絲愧疚。他當時提問的原因極富人性也很單純,如果約會的對象是個保守的教會女孩,吃完飯後就要隨意找個理由放鳥對方。因為不好玩。
現在羅伊也會跟著妻子雙手合十才開飯,彼此都明白活得越久,得感謝的對象就不斷地增加。至少現在,他們感謝飯桌上有另一個人的陪伴,有新鮮的牛奶可以泡咖啡。
新聞播報還在繼續,妻子朝電視說了一聲「關掉」後,屋內瞬間回歸到只有咀嚼聲的狀態。
「今天早上麒麟花開了。」
「媽送來的那棵嗎?」
「嗯。雖然有刺我不太喜歡。」
「老人家都喜歡那種紅吧。」
羅伊喝了一口咖啡,接著說。「不用擔心。」
蛋黃扎破後流到了潔白的瓷盤上,妻子放下手上的吐司,托起臉頰盯著羅伊,像是想講些什麼卻遲遲沒有開口。神性合一聯盟底下成員前些日子刺傷許普諾斯公司員工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羅伊猜想妻子一定是看到新聞,才會擔心身為研究員的他的安危。但是這些擔心都是多餘的,不會發生的事情就是不會發生。
門鈴聲響起。羅伊接過妻子遞給他的衛生紙將嘴角的碎屑擦拭乾淨後走下樓應門。按門鈴的是一位年輕樣貌的男性機械人型,身上深綠色的制服左胸前繡著大紅色的「郵」字,右邊臂章上繡著一隻灰雁,底下有個小小的「政」字用金黃色的線縫成。直到上個月底,竹水城裡的公部門郵差已經正式全面替換成機械人型。
羅伊接過郵差的信,下意識的向他說了聲謝謝。機械人型原本一腳已經跨上機車,聽到他的聲音又馬上轉身回來,掛著笑容走到羅伊面前仔仔細細地說了聲「不客氣」後才重新跨上機車,噗噗噗噗地騎走了。
羅伊久違地想起小時候總會在清晨出現,為每戶人家送羊奶的阿伯。剛開始他心裡對機械郵差全無好感,現在反而有一種複雜的情緒,害怕要是接受了新時代的東西就是對舊時代的背叛。之前的人類郵差也是個阿伯,偶爾晴朗的日子會踢下機車側柱和羅伊聊上幾句,說他這裡腳酸、那裡腰痛。
手上這三封信他已經閱讀過無數次了,每次收到後還是都令他無比哀傷。第一封第二封是尋常的水費電費,羅伊走上樓,將第三封寫著妻子名字,附註「本人開啟」的信件交給妻子。
無助的情緒從他們兩個眼中一閃而過。妻子深深吸了一口氣,「唰」一聲將信封拆開在面前攤平。然後雙手往大腿上一放,盯著腳上自己縫製的米黃色布拖鞋發呆。
即便羅伊不想問,但他還是得出聲。這是每日的例行流程。於是他開口,妻子把信重新摺好遞給他。信件內容簡短扼要,說明妻子的生育許可依舊不在這期的釋放名單中,還請靜待佳音。羅伊看完信,抱住有些頹散的妻子。過了好久她才勉強開口說出「你上班要遲到了。」這一句話。
羅伊讓妻子坐著,起身收拾完餐桌才走進書房拿公事包。然後咚咚咚咚地跑下樓,突然又像想到什麼似的跑上客廳,對著仍坐在椅子上的妻子說,「我會陪妳等到那一天的。」
直到聽見關門聲妻子才稍稍回過神來。她將那封信件收進座位前方的抽屜裡,在這之前抽屜中已經有十一封同樣的信件。闔上抽屜後她將碗盤洗乾淨放在架上晾好,然後走去客廳外的陽台澆花。
陽台上已經沒有烏頭翁來過的痕跡。仙客來和長壽花都已經開了,角落裡那盆錘絲海棠隱約冒出幾朵花芽,錘絲海棠上面吊著羅伊母親送給他們新居落成的麒麟花。她給每一株有開花、沒開花的盆栽都澆上水。然後想起羅伊,只好轉過身、背著戶外蹲下把臉埋進膝蓋裡偷偷掉眼淚。
「好,去買菜吧。」
*
羅伊關上門時總會習慣性的往二樓的花圃看去,就像是在確認季節變化似的。然後視線平移,永遠無法完工的巨大防護牆就在城市遙遠的另一方。那裡過去曾有著山的稜線,現在只剩下防護牆工期不一所導致的凹凹角角。
他得走了。手上的錶指針顯示七點四十二分,再過約一分半妻子就會走上陽台澆花,必須趕在那之前離開這條街道。腕上的錶是他大學入學時期父母送的,到「現在」也已經戴超過十一個年頭。往後的五十幾年裡,他再也沒有戴錶的習慣,但如今走路時隨著手臂擺動,手腕上的沉重感還是不斷提醒著他年輕時的回憶。那些建構起他成長的日子。
只有在妻子起床離開臥室後,關上房門的那一瞬間,羅伊的一天才正式開始。像斷電又突然通電的機械人型那樣「啪」地醒來。錶放在床頭右側的五斗櫃上,指針剛巧從六點九分跨到十。
接著他會起床盥洗。妻子也會走回臥室,兩人一起在鏡子前打理惺忪的臉龐,然後獨自出去準備早餐。約莫是扣襯衫鈕扣的時候門外會傳來新聞播報的聲音,羅伊已經聽到倒背如流。
「昨日傍晚,西聯合國發表聲明,關於北海的環境問題……」他扣上第一枚鈕扣小聲的念著,語句節奏和電視主播幾乎完美貼合。
「……東亞聯邦拒絕承認這項協議。同時,第三勢力的國家也對美國是否會遵守協議紛紛表示懷疑。」接著是第二枚、第三枚。
「接下來焦點回到國內。為您播報下一則新聞:昨日由神性合一聯盟於中央大道上舉行的反〈VR法〉集會大遊行……」羅伊扣好最後一枚鈕扣,轉頭看向窗外,一隻烏頭翁快速地從眼前掠過。
「羅伊——」妻子喊。
他把每一段對話,每一種結果詳細地記在書房裡陰暗的狹小儲藏室內。今天是「星期三」,自由活動日。同時也是來到這裡的第一千七百四十四天。
公事包裡裝著一條汗巾、一把電子傘、掛載自動濾水器的智能水壺以及一卷二零七七年由金蘋果公司出產的伸縮型卷軸式電子地圖,收納起來後只有一枝鋼筆的大小及重量。最後還有一把折疊鋼刀。羅伊覺得刀這種東西莫名的有股歷史的厚重感,幾千年前人類發明用來自我防衛或迫害他者的道具,在科技大幅進步,舊觀念、舊器物逐漸被淘汰的現代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這大概就是人類為數不多且亙古不變的幾個核心原則之一吧。暴力。
他繼續穿越過幾條街道,心想差不多要到了妻子哭泣的時刻。剛到這個世界不久時,有一次他出門後不知怎地興起一股偷窺的欲望。於是跑上對面住宅的二樓,隔著窗簾偷看妻子的舉動。雖然隔著窗戶和窗簾,他依舊可以隱約感覺到妻子蹲著的時候一定哭了。偶爾羅伊心底會感受到莫名的憂傷,但他說服自己一定是因為整條街上乃至於整個城市都空無一人的緣故。
他花了快一年的時間才確認了這個事實。然後了解到這個世界的核心就是妻子本身。一切事物都只不過是她潛意識裡記憶的具象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這座城市裡,妻子的高中母校從走進校門前的一花一木,到教室裡講桌櫃深處五顏六色的粉筆都一應俱全;而羅伊的高中母校只是一團灰樸樸的色塊,像是幼稚園兒童少了父母幫忙隨意塗鴉的暑假作業。
原因就在於妻子並沒有走進去過他的學校,只留有模糊的印象。羅伊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心裡有些複雜,因為灰樸樸的教室除了樣貌醜陋以外,還有一股青春期男性的汗臭味。他下意識舉起自己的手臂聞了聞腋下。
城市裡有許多地方和他的學校一樣呈現模糊色塊的狀態,穿過的時候就像走進一團由電子雜訊組成的雲霧之中,這個時候他手上的地圖會暫時失靈,標記著「現在位置」的紅點像強風裡的蠟燭快速地閃滅不斷。有一次他騎著機車在雲霧裡整整彌留了一個晚上(雲霧裡依然有白天黑夜之分)找不到出路,絕望的他閉上雙眼等待著意識的死亡。誰知道一睜開雙眼看見的還是那隻機械錶從六點九分跨到十分的畫面。
那次瀕臨崩潰的恐怖經驗反而加速他探索世界的腳步。羅伊明白無論自己遭受了什麼樣的變故,只要手上的錶針走到凌晨五點二十三分,他就一定會回到那張有著妻子熟悉味道的床上,然後可以用手撫摸左側床鋪上被她身體壓褶出的床單皺痕以及皺痕裡殘留的溫度。羅伊坐起身,盥洗,仔細地扣好白襯衫的鈕扣,繼續尋找脫離這個世界的方法。
*
因為是自由活動日的緣故,羅伊暫時停下探索城市的工作。他將機車停在郊外電車車站的入口後獨自走了下去。他來這裡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對在原本熙來攘往的地方睡覺的感覺上癮,就像以前夜遊的大學生總愛坐在大馬路的雙黃線上拍照一樣。
車站裡總是有燈,這讓羅伊非常困擾,但這只要一把電子傘就可以解決。真正讓他感到彆扭的是上廁所的時候,車站男廁在這個由妻子潛意識所構築的世界裡,毫無意外的也是一團模糊的色塊。但是羅伊偶爾也會想,要是車站男廁清晰可見,恐怕才是真正需要擔心的地方吧。
他精準地將尿撒在軌道上後,打開電子傘,將傘幅調成最大,切換成夜空模式。然後把公事包枕在後腦勺當作枕頭。
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羅伊偶爾會夢到現實生活中的瑣碎片段。可笑的是,夢裡的那些現實比起「現在」足足還要晚了五十年之久。
他今天也做夢了。一如往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