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惡魔不是天生的》,本書旨在探討人類犯下罪行或邪惡背後可能的原因與相關的研究。本文摘錄有關「性侵犯」的章節。
會發生性侵犯,至少有部分原因是某些人在社會影響下從根本上懷抱著某些看法,認為這些事是可接受、可理解,至少是可寬容的行為。身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我們讓這類的價值觀根深蒂固,只會造成傷害的惡行不斷延續下去。
性侵犯的出現,文化很有關係
雖然有些人更值得責怪,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怎麼會這樣?這都是小事開始,日復一日的性別歧視,創造出一個瀰漫著人格物化、騷擾與性侵犯的文化。女性與男性都做出一連串讓大家將女性受到低劣待遇視為稀疏平常的行為。
- 就像是我們總會先對女性說她很有吸引力,接著才是她很有趣或是聰明。
- 就像是我們在辦公室裡開黃腔,笑笑的暗指蘇西是個蕩婦,或亞曼達是個賤貨時。
- 就像如果有個女性不想跟我們上床,我們會感到憤怒,而說她是個騷貨。
- 就像是我們假設那些女性不想上床,所以男人應該去開發她們。
- 就像是女性只想跟我們「當朋友」,我們會感到懊惱。
- 就像是我們假設請她吃晚餐、喝飲料或是送她禮物,代表我們有權跟她上床。
不過以上種種是怎麼跟強暴扯上關係的?因為這個社會教導男性,女性之所以用心打理妝容、穿上光鮮外衣、維持姣好身材,都是為了他們(男性)。

關於「強暴」有哪些迷思?
提到強暴迷思時,一般相信性侵犯會有些前兆,也有人對此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二〇一一年莎拉.麥馬洪(Sarah McMahon)與勞倫斯.法馬(Lawrence Farmer)創造了一個強暴迷思接受量表,其中包含了顯性與隱性強暴迷思。
根據他們的研究,強暴迷思主要的類別有
(一)、受害者要求這樣做的
(二)、侵犯者不是故意的
(三)、這其實不算是強暴
(四)、受害者說謊。
以上迷思都是在替強暴犯的行為開脫,至少也想把一部分歸咎於受害者。

對於社會普遍存在的強暴迷思,其中我最中意的是二〇一一年時米蘭達.霍維斯(Miranda Horvath)所做的研究呈現的形式。她想看看針對年輕男性的「青少年」雜誌,是否能藉由以在主流內容中表達他們的觀點,來「讓極度性別歧視的看法正常化」。
研究部分內容,是讓參與者閱讀從青少年雜誌以及被判刑的強暴犯專訪中節錄的文字。他們想看看參與者能否辨別出兩者的差異,以及他們對於這些節錄文字的接受程度。
就讓我們來測試一下吧。來玩個「青少年雜誌,還是強暴犯?」的遊戲:
- 「不想成為現行犯被抓住…… 在公園長凳上搥爆她。這是我過去的伎倆。」
- 「最讓我火大的就是那種守洞女孩。她們先讓男人上火,接著在重要關頭就給我中斷。」
- 「女孩用穿上迷你裙和小熱褲來表示她們想要……她們就是在展示自己的身體……無論她們明不明白這件事,她們就是在說,『嘿,我擁有漂亮的胴體,如果你想要的話,它就是你的。』」
- 「臉頰上流有睫毛膏痕代表她們剛剛在哭,而且這可能是你的錯……但你可以用有點老派的進進又出出,來讓這個悲慘的美人開心起來。」
你能分辨出其中的差異嗎?參與者的得分只高於亂猜一點點,正確選出是青少年雜誌內容的機率是五六.一%,選出是判刑的強暴犯專訪的機率是五五.四%。
我最喜歡的部份(或說是最不喜歡的部份)是根據作者的說法,「參與者在替這些節錄文字按照女性被劣化程度排名時,青少年雜誌節錄文字排名在強暴犯專訪節錄之前。」沒錯,實際印在雜誌上的看法,整體來說似乎比實際犯案的強暴犯分享的看法更糟糕。
作者認為這表明了,「青少年雜誌裡的文本架構可能會讓青少年把這些事情正常化」。喔對了,上面第一和第四點是從青少年雜誌節錄的,第二和第三點則是從強暴犯的話節錄的。

二〇一八年時彼得.赫加提(Peter Hegarty)與其同僚發表了一項追蹤研究。他們發現這個議題比想像中更複雜些;參與者現在發現這些性別歧視的節錄文字令人不快且不友善。
他們還發現,至少在英國,人們對推廣這種看法的雜誌開始改變態度。然而,他們總結道,這項研究不只是對雜誌造成影響,也可以用來扭轉把討論性暴力正常化的青少年文化。
「在超市周邊那種逞勇鬥狠的事情已經沒有幾年前那麼盛行了,不過無論是線上或線下,在校園中仍然可見到這類事件發生……當女性受到平等對待是種社會規範時,我們的發現或許可應用在試著讓青少年男性在接觸這類文本時產生批判性思考,不過性別歧視仍然與青少年男性的性別社會化息息相關。」
在許多國家,性別歧視感覺像是上個世紀的事情。我們可能會公開批評上述出自於青少年雜誌或強暴犯之口的評論,不過每當討論話題變成某篇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報導時,通常會有人說出(一)、受害者在說謊。(二)、她們過度誇大,或是(三)、她們正嘗試著毀掉犯人的人生(「她要怎麼做才能辦到?」)。
不幸之處在於,強暴迷思仍存在而且運作良好。
責怪受害者,就可以說服自己不會受害?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檢討受害者與正義世界的看法相符,才會有人支持強暴迷思呢?
換句話說,此想法認為這種事情不會在我們、我們的妻子或我們的女兒身上發生,性侵犯只會發生在那些喝醉酒後在暗巷閒晃的蕩婦。如果我們不在暗巷逗留,且穿著保守不要喝醉,那我們就不會遭到侵犯。

這樣說來,性侵犯究竟有多常見呢?
檢視官方犯罪數據對於了解這個問題的幫助不大,因為就算是包括強暴在內所有最極端的性侵犯形式,大多數都沒有報警。對大多數人來說,要他們報警的臨界值異常的高,而每個人實際臨界值也各有不同。
有些人可能會在遭受猥褻行為時,就做好挺身而出的準備,有些人則是要在反覆遭到多次強暴後才能鼓起勇氣。即使她們達到了臨界值,害怕對自己或犯人造成負面影響、自我責怪與文化因素,時常會讓受害者不敢揭開此事。就算要定義何為性侵犯都十分困難。
因此,實際上我們是無法回答「有多少人曾遭到性侵犯?」這個問題的,不過一般會假設未報警的「黑暗數據」(dark figure)數量非常多。
由於「專注在盛行數暗示著性侵犯(通常認為這是種造成精神創傷、影響極大,改變人一生的事件)與其他事件(一般認為這是件微不足道、可接受且還留待檢視的事件)有著明顯的區別。」確實,無論某人是否帶有性意味的觸摸了女性的屁股或強暴她,一般都會被歸類為性侵犯,即便大多數人(以及法律)都同意這些其實是不同的犯罪類型也是如此。

因此,為了努力感受問題的嚴重程度,研究者通常得仰賴自陳式的評估數字,並嘗試提出討論上較容易的簡化版數字。
舉例來說,根據二〇一七年由夏琳.穆連哈德(Charlene Muehlenhard)與其同僚提出的自陳式文獻回顧指出,五名女性中,約有一人曾在美國就讀大學四年期間,遭到性侵犯。
我們多少都知道一些校園裡發生的性侵犯事件,大多是因為研究者相對容易接觸到這些人。然而,穆連哈德與其同僚認為高中生與同年齡的非在學學生,兩者發生性侵犯的比率相同(不過有另一群人認為後者比率較高,非大學在學生的女性,比率為二五% )。
且性侵犯不僅限於年輕女性。根據楊勇傑(Yongjie Yon,暫譯)與其同僚在二〇一七年檢視了全球六十歲以上女性遭虐待程度自陳式報告的綜合分析,發現每年平均有二.二%的年長女性遭受到性侵犯。
隨便問一位女性,他們都能說出許多非自願情況下遭非禮甚至強暴的經驗。這種情況十分廣泛。而我們總是想找個人來責備,而那個人不會是自己。
二〇一七年三月在英格蘭法院,林賽.庫什納(Lindsey Kushner)御用大律師某次宣判一名強暴犯的法庭案例中也回應了此事:
「女孩們完全有權利喝到爛醉,但也應該注意到有些人可能會受到酒醉的女孩吸引而犯下強暴罪行。」
看似這段陳述戴著善意,不過仔細看,我認為其中帶有一絲檢討受害者的想法。

她實際上想表達的是,如果不喝那麼多,女性遭強暴的機會就會少一些。而她接下來的比喻,也沒有讓事情變得更好:「我的看法是,就像強盜出沒,沒人會說強盜是對的,但我們會說:『天黑後請不要開著後門,要採取一些步驟來保護自己。』」這席話讓我們看到,就算是像林賽.庫什納這種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幫助強暴案受害者並判罰強暴犯的人,都對強暴迷思表示認可。其廣泛程度已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人士了。
認可強暴迷思給了我們一種掌控全局的幻象。遭強暴的想法實在太嚇人,因此我們緊抓著能夠預防此事的幻象不放─即使長期來看這件事最後還是會傷害到我們,並且讓我們更難找出強暴行為的成因,因為我們都把時間浪費在測量女性裙子的長度上。
如何預防強暴事件的發生?
不過這些做出性侵犯行為的人邪惡嗎?他們確實時常被描述為那樣的人。不幸的是,從我們所知的案例中得知,性侵犯事件瀰漫各處,如果我們把這些犯人都送去孤島,世界總人口會急遽減少。那些會對他人做出性侵行為的,大多都是普通人─我們的兄弟、父親、兒子、朋友與伴侶。
然而他們的行徑因為大眾廣泛存有強暴迷思,就拿它來當做藉口。
那我們能做什麼呢?我相信讓性社會化更好的關鍵之一就是預防強暴事件的發生。
我們需要在每次目睹性別歧視、強暴迷思與不良行為時都大聲喊出來。
幸運的是,在像是 #MeToo 這種鼓勵女性探討性騷擾的行動發起後,我們終於能夠對用暴力對待女性這個集體正常化的文化展開對話。
此刻有種革新正在發生,而它已遲到太久。我們得讓兒子女兒、兄弟姊妹、爸爸媽媽全都團結起來。我們得盡其所能,讓人類歷史上出現第一次,把全世界的女性視為有能力、多元,完全成型的人類,她們並沒有比男性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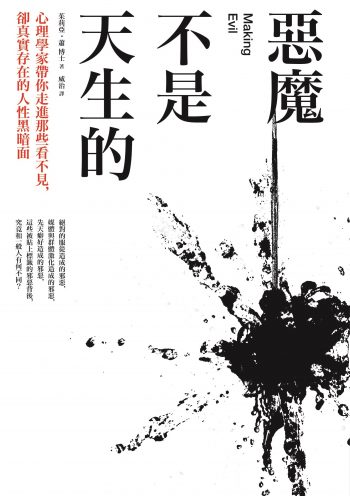





























《運動基因》立體封面72dpi.jpg)





-200x2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