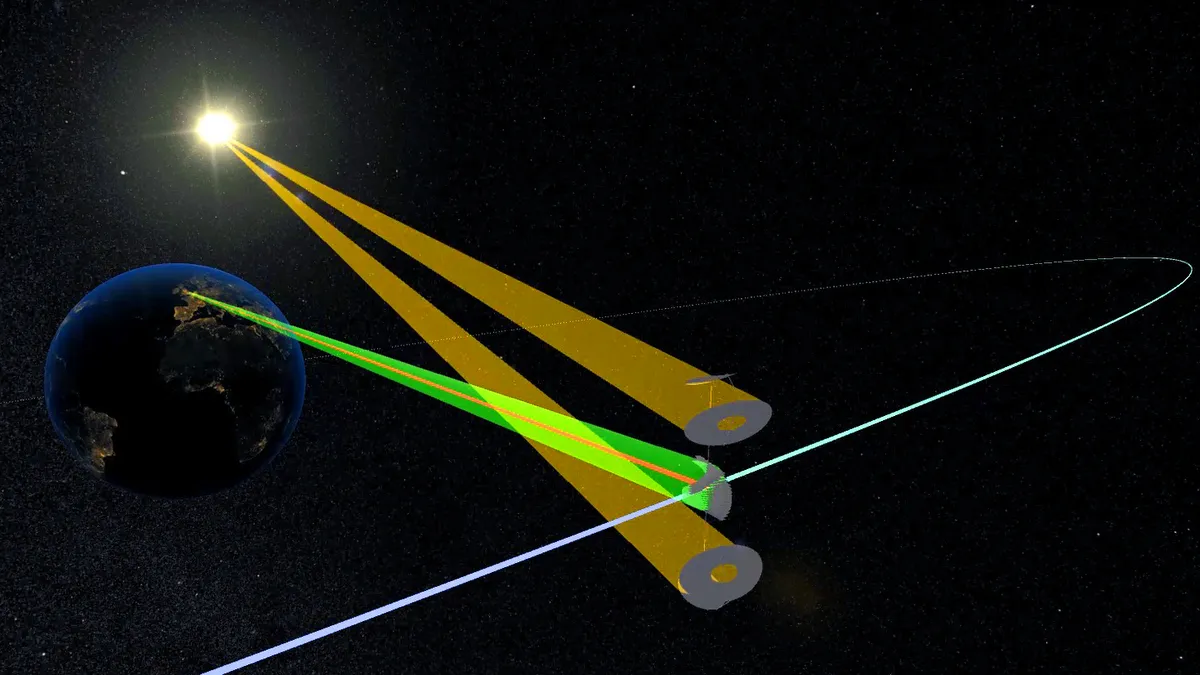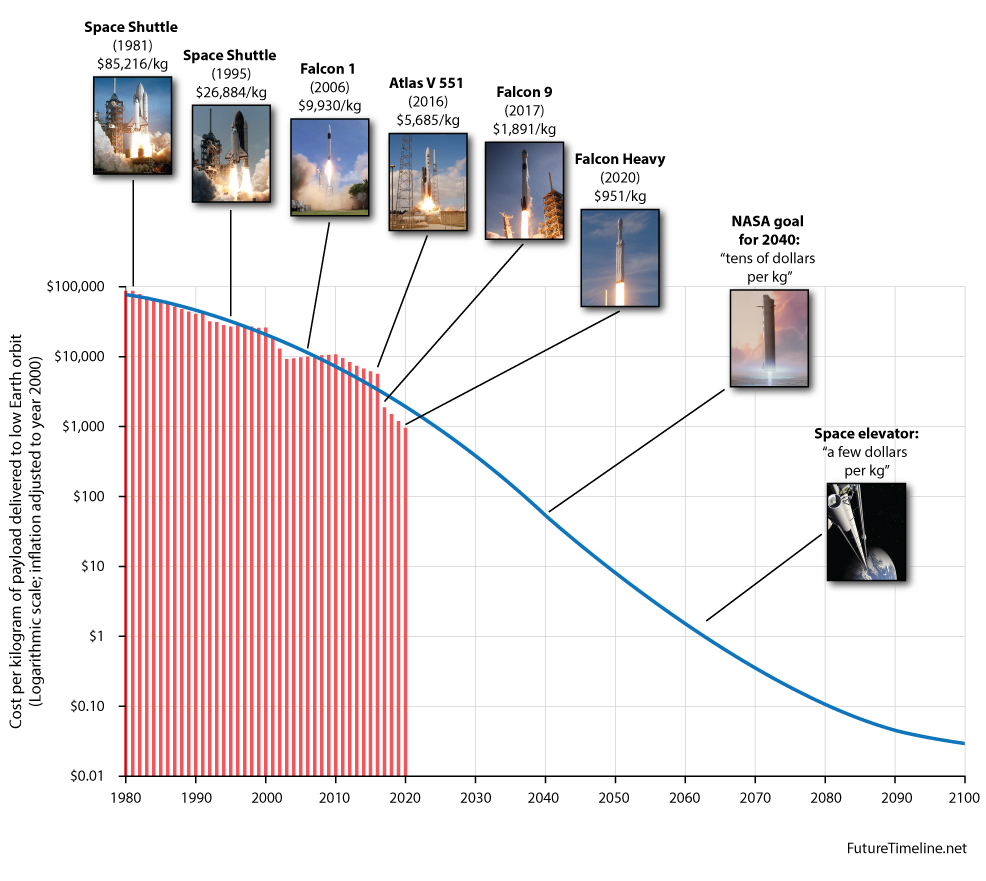用合成生命來救援
但是,如果變化是來自這些勢力強大的石油巨頭本身呢?二○一○年,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Mobil)研發部副總裁埃米爾.雅各布斯(Emil Jacobs)宣布一項前所未有的計畫:撥款六億美元,以六年時間致力開發新一代的生物燃料。當然,上一代的生物燃料(主要為玉米乙醇)
美國能源部說,藻類每畝可生產的能源為傳統生物燃料的三十倍;同時,藻類幾乎在任何死水中都能生長,因此幾個大型發電廠正在測試以此作為二氧化碳吸收器,把煙囪接駁至池塘,讓藻類消耗二氧化碳。這是個相當誘人的可能性;然而,為了讓這個可能性簡直是一場災難。這些燃料對環境造成相當嚴重的危害,並且移除了數以百萬英畝的農作物,造成食品價格飆升。但艾克森美孚的生物燃料並非以糧食作物為基礎,也不如第一代生物燃料技術需要大量土地支援。相反地,艾克森美孚計畫以藻類開發生物燃料。
成真,艾克森美孚已與生物學壞小子克萊格.凡特及其最近成立的合成基因組學公司(Synthetic Genomics Inc.)共同投入研究。
為了研究藻類養殖方法和採油技術,艾克森美孚與合成基因組學公司在聖地牙哥建立了一個新的測試基地,凡特把它稱為「水藻中途之家」。二○一一年二月,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到了該處參觀。從外面看來,這個基地看來就像個高科技溫室:透明塑料窗格、白色支柱,和一道道氣閘門。我們經過這些閘門時,負責主管這計畫的保羅.路斯勒(Paul Roessler)向我解釋基本運作原理:「我們的生物燃料必須擁有三個要素:陽光、二氧化碳和海水。使用海水是因為我們不想占用農地或瓜分農業用水。二氧化碳則是更重大的議題。這正是何以隔離與封存二氧化碳會如此重要:這麼做既能減緩全球暖化,也提供了集中的能源來源。」
我們走過另一道門來到主房間,這個足球場大小的區域沒有太多裝飾,只放了六大桶水藻,以及一張掛在牆上的巨幅「細胞的生命」海報。路斯勒指著海報說:「我不知道你還記得學校課堂教的多少東西,但光合作用是植物將光能轉換成化學能的過程。白天,植物利用陽光將水分解成氫和氧,然後將之結合二氧化碳,結果就成為碳氫化合物燃料,稱為『生物石油』。到了晚上,植物通常會利用這些燃料做細胞修復。我們的目標是能確實地大量生產這些生物石油。」
一同參觀的凡特此時也加入對話:「路斯勒說得太謙虛了。事實上,他已找到方法,讓藻類細胞自願分泌收集到的脂質,使藻類變成微型工廠植物。」路斯勒進一步解釋:「從理論上來說,技術一旦完善,我們可以不斷重複運行此程序,不斷收取生物石油。這些細胞只會不斷生產出石油,而且你無需收割所有細胞,只需收集細胞排出的油。」
這效率是相當可觀的。「相比起傳統的生物燃料,」凡特說:「玉米每年每畝生產十八加侖;棕櫚油每年每畝大約六百二十五加侖。我們的目標是利用這些改良的藻類,達到每年每畝一萬加侖的生產量;同時,在二平方英里的設施中讓這些藻類勤奮地工作。」
要了解凡特的目標是如何雄心勃勃,讓我們來做一下計算:二平方英里相等於一千二百八十畝,而在每畝生產一萬加侖燃料的情況下,就等於每年能生產出一千二百八十萬加侖的燃料。今天每加侖的石油平均能跑二十五英里,一輛車平均每年跑一萬二千英里,因此二平方英里的藻類農場所生產出的燃料足夠推動大約二萬六千輛汽車。因此,要多少畝的藻類農場才能推動美國所有車輛?今天美國大約有二億五千萬輛汽車,所占面積約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平方公里,相當於美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四九(或占內華達州約百分之十七的面積)。試想,當我們的汽車每加侖可跑一百英里,或我們當中開始有越來越多人轉用電動汽車時,會發生什麼事。
就算合成基因組學公司達不到這目標,艾克森美孚也並非這場競賽中的唯一球員。舊金山灣區的LS9能源公司(Life Sustain 9 Billion, Inc.)已經和雪佛龍能源公司(Chevron)以及寶僑公司(P&G)共同研發生物燃料。而在不遠處位於加州的愛莫利維爾市,阿米瑞斯生物技術公司(Amyris Biotechnologies)也與殼牌石油公司達成同樣的合作。波音公司(Boeing Company)和紐西蘭航空公司(Air New Zealand)亦已開始發展以藻類為基礎的飛機燃料,其他公司甚至走得更遠。維珍航空公司(Virgin Airlines)已開始部分使用生物燃料(椰子油和棕櫚樹油)讓七四七飛機航行於天際。二○一○年七月,總部位於舊金山市的太陽酵素公司(Solazyme)更已經供應美國海軍一千五百加侖以藻類為基礎的生物燃料,並且獲得一紙十五萬加侖供應合同。與此同時,美國能源部正資助三所不同的生物燃料研究機構,而追蹤可再生能源市場成長情況的清潔能源市場研究公司(Clean Edge)在其第十屆年度產業報告中,概述全球生物燃料的生產和批發價格,在二○一○年已達五百六十四億美元,預期到二○二○年將增至一千一百二十八億美元。
顯然,市場前所未有地對碳中和、低成本的燃料感興趣;不過,問題依然存在。上述提及的每一家公司(或未提及的競爭者)全都未能找到將這種技術大規模生產的竅門。朱棣文部長說,要真正滿足我們的需求,生產規模必須以百萬、甚至千萬的倍數增加。但是,他也同時指出,研究生物燃料的同一批科學家過去也曾成功提升如抗瘧疾藥物之類物品的產量。「所以,這目標是有可能達成的,」他說:「考慮到參與計畫的科學家的素質,我樂於相信這目標有可能達成。」 為了滿足能源需求,美國能源部並未把所有賭注押在生物燃料上。該部門對於「破解光合作用」也有興趣。朱棣文部長提倡的太陽計畫,正在資助由人工光合作用聯合研究院(Joint Center for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一個由加州理工學院和勞倫斯.利福摩爾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共同領導,經費達一億二千二百萬美元的多機構合作研究計畫。該中心的目標在開發所有人造光合作用的必要組件:光吸收劑、催化劑、分子連接器,以及分離膜。
加州理工學院永續能源技術研究院(Calte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Energy Research)主任及該計畫主要科學家之一,哈利.阿沃特(Harry Atwater)博士說:「我們正在設計一種人工光合作用過程。我所謂的『人工』,是指整個系統中不涉及任何有生命或有機的成分。我們基本上是將陽光、水和二氧化碳,轉化為可儲存運輸的燃料─我們稱之為『太陽燃料』,以解決太陽光電未能照顧我們其他三分之二能源消費需求的問題。」 阿沃特認為,這些太陽能不單可以用來驅動我們的汽車、為我們的大廈提供暖氣,也能讓光合作用的效率增加十倍,或甚至一百倍─也就是說太陽能可以完全取代石化燃料。「我們正在接近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他說:「很有可能三十年後,每個人都會說:『天啊,我們過去為何會為了製造暖氣和能源而燃燒碳氫化合物?』」
儲存的聖杯
我們之所以如此依賴碳氫化合物,除了是因為它們具有能量密度高與易取得的特性,也是因為它們易於保存。煤礦安坐在管道內,石油存放在油鼓裡。然而,太陽能卻只在有陽光的時候才管用;而風力則只在風持續吹拂時才能產生。這樣的限制仍然是廣泛採用可再生能源的最大僵局。直到太陽能和風力可以提供全年全天候可靠的基本荷電力,否則兩者都無法提供顯著的能源供應量。發明家巴克敏斯特.富勒曾在數十年前提出建構全球能源電網的想法:在地球陽光普照的一面收集太陽能,供應這個星球黑暗的一面所需的電力。然而,大多數人把希望寄托在建立能夠儲存「牢靠」、「時間轉移型」的能源的大量本土電廠,也就是說,白天時收集能量,在夜間釋放之。從此,這就成為綠色能源運動的聖杯。 最終來說,除非我們能夠儲存太陽能,並且以從未達到的規模儲存,否則太陽能即使再廉價也沒有意義。要達到相當於現有輸電網絡規模的太陽能儲存量需要數量龐大的電池,但今天的鋰電池卻遠遠不夠用;它們的儲存容量需增加十到二十倍。而且,如果我們真希望可以增加電池數量,就必須以地球上存量豐富的元素來製造;否則,我們只是把對進口石油依賴的經濟,轉換為對進口鋰依賴的經濟。
值得慶幸的是,事情已有所進展。近來,儲存太陽能的技術已獲得足夠改善,並且引起風險資本家關注,其中的領軍公司為凱鵬華盈創投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這公司的投資項目逾四百二十五宗,當中包括美國線上、亞馬遜、昇陽電腦,美商藝電(Electronic Arts)、基因泰克和谷歌等公司。從這些投資標的就能看出,凱鵬華盈有挑選業界佼佼者的習慣。而由於該公司要角約翰.多爾(John Doerr)向來就對環境以及對抗全球暖化議題非常熱中,因此他們選擇投資的許多公司皆已進軍能源領域。
二○一一年冬天,我向比爾.喬伊更新有關儲存太陽能的進展報告;喬伊是昇陽電腦創辦人,現任凱鵬華盈在綠色能源領域的重要合作夥伴。他告訴我,最近兩個投資項目旨在轉變市場:首先,普利茅斯能源公司(Primus Power)正在製造可充電的「液流」電池,其電解質流經整個電子化學電池,直接讓化學能轉換為電能。這設備已經使得位在加州莫德斯托的嶄新能源儲存系統(該系統價值四千七百萬美元,儲存了二千五百萬瓦、七千五百萬瓦小時的電力)得以穩固地儲存風力。凱鵬華盈公司的第二個賭注是阿奎諾能源公司(Aquion Energy)。這公司所製造的電池類似今天的鋰電池,但卻有個重要的變革─這種電池並不是依靠鋰這種有毒、數量稀少的元素,而是使用兩種價格便宜且無處不在的成分─鈉和水。這兩種成分的附加好處在於,它們既不會致命,也不易燃。這種電池能平穩地釋放能量,無腐蝕性,而且使用的是地球上豐富的元素,而且實際上甚至安全得可以吃進肚裡。
「使用這些技術」喬伊說:「我估計存取每千瓦小時電力所需的總成本只要一美分。所以,我可以把間歇性的風能連接到阿奎諾系統,將風能的製造成本穩固在約每千瓦小時一美分。而這金額包含了所有成本。幾年後,你會在市場上看到這些產品;在那之後,我們再沒有理由認為我們無法擁有可靠的、相當於現有輸電網絡規模的可再生能源。」
世上最權威的固態化學學者之一、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唐諾.薩多偉(Donald Sadoway)也看好未來的電網規模儲存技術。他在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能源部和比爾.蓋茲的資助下,發展並展出了液態金屬電池(Liquid Metal Battery)。他最初的靈感來自煉鋁廠的高電流密度及龐大規模。液態金屬電池之內的溫度熱得足以令兩種不同的金屬處於液體狀態。其中一種是密度高的金屬,如銻,它會沉到底部;另一種是密度低的金屬,如鎂,會浮在上層。在它們之間是有助於電荷交換的熔融鹽電解質(molten salt electrolyte)。結果他做出了電流較現今最高端電池高出十倍的電池,而且它簡單、價廉的設計使得存入一千瓦小時的電力只需二百五十美元─只為現行鋰電池不到十分之一的價格。薩多偉的設計也顧及規模。
「今天液態金屬電池的原型是一顆曲棍球的大小,足以儲存二十瓦特小時的電力,」薩多偉說:「但我們正在研發較大單位的電池。想像一下,一顆冰箱大小的電池就足以儲存能夠供應你家一天需求的三十千瓦小時電力。我們的設計概念是『裝上後就忘了它』:能夠在不需要人力維護的情況下運作十五至二十年。它便宜、安靜、無需維修、不產生溫室氣體,並且由地球上豐富的元素製成。」以每千瓦小時二百五十美元計,一顆家庭用液態金屬電池要價七千五百美元。以十五年攤分,再計及成本和安裝費用,一顆家庭用液態金屬電池每個月花不到戶主七十五美元。
然而,這系統真正過人之處在於它擴充尺寸的能力。一顆貨櫃大小的液態金屬電池,足以供應一整個街坊的電力;一顆沃爾瑪大賣場大小的電池,足以支援一個小城市。「在未來十年,我們計畫推出貨櫃大小的液態金屬電池,緊接著會再推出家用電池。」薩多偉說:「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到達那裡的路,而且也不需要奇蹟般的突破。」 當然,解決儲存問題就會為太陽能和風力發展帶來重大突破。但接下來,該如何處理那些骯髒的燃煤發電廠就成了真正的問題。對此,比爾.喬伊也有想法:「很難相信電力公司會關閉一個已完全攤銷而且每天仍能賺錢的資產。我們應該做的是倒轉模型,把燃煤發電廠當成緊急備用發電裝置。我們可以百分百依賴可再生能源來應付基本能源需求,但當天氣預報說我們將面對真正的問題時,我們就能啟動燃煤發電廠。我們只向電力公司支付維修與偶爾運行這些發電廠的費用,就像你使用緊急發電機那般。」
摘自PanSci 2013年8月選書《富足:解決人類生存難題的重大科技創新》,由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