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取自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畫面
下地坐草──古代女人不躺床上生孩子
「夫人,用力、用力,看到孩子的頭了!」產婦躺臥床鋪,產婆不停掀開厚被檢查。這樣的臨盆場景,我們常在中國古裝劇見到。但如果比對醫書文獻,畫面也許有點 bug——古代婦女最尋常的分娩方式並非平躺床鋪,而是半蹲在地面、上身直立著生孩子!
「古時婦人產,下地坐草,法如就死也。」從南北朝醫家的這段話就能看出,女人分娩不僅性命攸關,而且是離開床榻、下地蹲坐著生產。地上會鋪草堆或獸皮,一方面避免嬰兒落地受傷,另方面也防止血水弄髒屋舍,觸忌犯神。
然而,生產是窮盡氣力的生死馬拉松,蹲踞垂直的姿勢好施力,卻很難支撐十數個小時。正因如此,產房內便需要數名「抱腰人」(又名「看產人」)幫忙。這些女性助產者一人站在產婦背後,環抱撐住她的腋下,讓產婦能安心倚靠;另一人則在產婦身前,準備迎接新生兒。古書裡罕見臨盆一詞,「分娩」也是宋代以後才較常用,1500 年前的人若說「抱腰」,就代表要準備替婦人接生了。
只是,生產如此辛苦,為什麼古人不在鬆軟舒適的床上呢?
李貞德推測,方便產婦用力、胎兒順行,應該是主要原因。此外,從唐代以前的文獻看來,床高可達數尺(一尺約 23 公分),南朝便曾有孕婦想流掉孩子,「自床投地」無數次。設身處地試想,對大腹便便的孕婦和協力抱腰的產婆們來說,躺在高床上生產,恐怕不是最佳選擇。當然,物質條件也可能需納入考量。古時生活不如現代優渥、方便,上網採購 24 小時送到家,床榻等家具遠比今日珍貴,若被大量血水浸透就報廢了。

圖/李貞德攝
逐月養胎,古代孕媽咪食譜
生育,不僅是女人九死一生的大事件,對男性社會來說,也是傳宗接代的關鍵時刻。從漢朝起,醫學對女性身體的照護明顯聚焦在「生育」,懷胎、分娩、產後,都有調養建議與禁忌規範。
大約在 5-7 世紀之間,這些持續積累的知識開始被歸納整合。在性別化身體觀的基礎上,漸漸趨向一致標準,奠定了中國婦產醫學在宋代獨立成科。
例如,漢代醫聖張仲景建議孕婦常服「當歸散」。南朝醫生主張懷孕七個月服用以丹參、人參、當歸等調製的「丹參膏」,幫助順產;但北齊徐之才卻說「丹參膏」太過滑利,應該到十月再吃。唐代孫思邈採用了徐之才的說法。到宋代,懷孕七月服用滑胎藥的說法,就不再流傳了。
另外,徐之才還提供精細的「逐月養胎方」,按懷胎月份建議產婦適合的穀物、肉類,再搭配藥方滋補。放到現代,大約就像孕媽咪「每月推薦食譜」,為胎兒每個階段的發展補充適當養分。
養胎有大吉,自然也有大忌。中國經脈觀於漢朝後確立,醫書也會提到懷胎逐月須避免的扎針穴位,以免不慎流產。
不吃醬油、不聽惡言,胎教傳統淵遠流長
多吃什麼小孩皮膚好,少碰什麼胎懷得穩,歷來有各式各樣的經驗傳承,讓許多現代準媽媽壓力沉重──媽咪不孤單,這種煩惱古代產婦也有!
古代醫方記載的不只草藥、針灸,還有今日看來的迷信偏方。因為在前科學文明的時代,「方」即為除疾保命之道,草藥是一種方、避鬼神也是一種方,都是為了護佑產家和產婦平安順遂,故而記載在醫方中。
以下這些,醫方也有。
孕期不宜吃醬油,孩子皮膚會黯黑。不要吃薑,以免生出似薑形、有六根指頭的小孩。想生兒子,就多看雄雞虎豹、耍刀弄劍;要生女兒,不妨戴耳飾、串珠子,玉佩響叮噹!若期望孩子乖巧善良懂禮貌,注意了,肉塊割不正不吃,坐蓆不正也不坐,非禮無視、勿聽、勿言──因為孕婦耳濡目染,經由「外象內成」,孩子也會受影響。
誰說古人和我們差很大?今日人們習以為常的「胎教」,一千多年前就已被寫入醫方,存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了。
李貞德提到,
這些養胎之道貌似不「科學」,其實反映了中國「氣的身體觀」。
當時的人以「氣」理解世界,天地蘊含氣、人也以氣為生,氣在萬物自然間流通,與我們的身體相互感應。外在醜惡或美善的人事物,其形、其氣會通過母親身體,影響胎兒。於是,便有士人這麼說:「諸生子有癡疵醜惡者,其名皆在其母。」小孩的品質,成為評斷孕婦言行舉止的判準。
媽媽心裡苦,古今皆同啊!
求孕、求男、求好男
從安胎、養胎到胎教,都是為了讓產婦不只好生,而且生得好──「求孕、求男、求好男」,畢其功於一役!
這一役,來到最緊要的決戰關頭「臨盆分娩」。
產家須提前準備場地,可能是屋中某一個房間,或者另外搭設產廬或產帳。產房的位置並不是隨心所欲,而要按照生產月份配合方位,趨吉避凶,以期順利平安。例如,「正月,天氣南行,產婦面向於南……大吉也。」
這一整套時間、方位相應的吉凶論,背後同樣蘊含著天人感應觀,時間、空間、人彼此相互影響。醫書中便出現「產圖」,正月、二月、三月……,讓產家根據分娩當月的產圖,準備生孩子的每個步驟歷程。


圖/唐代王燾《外台秘要》收崔氏十二月圖
到了待產時刻,抱腰人(助產婦)已隨伺在旁,陪伴安慰產婦,幫助按摩放鬆,產婦可或坐、或臥、或走動,舒適為主。何時開始發力?現代醫療用「開幾指」為標準,古代判斷依據則是「有多痛」。過早用力,很可能體力不濟;須等到產婦痛得不得了「腹痛連腰脊」,代表已接近臨盆,才能開始下地坐草使勁。
整個產程即使順利也要十幾個小時,產婦蹲坐分娩、抱腰人一前一後助產。如果人手不夠或產程過長,就需要輔具上場,例如日本江戶時代的古裝劇裡,用衣帶懸樑、綁縛在孕婦手上,或者垂吊橫木,幫助她倚靠用力。日治臺灣的陪嫁品中有生子桶,讓產婦蹲坐其中,攀附桶子邊緣支撐施力。早期香港華人嫁妝也有稱為「子孫桶」的馬桶,大概也是作為生產輔具。
孩子生下了,快抱開!
孩子平安降生後,又是什麼情況呢?
古裝劇裡常這麼演:產婦費盡氣力生下寶寶,虛弱急切地說:「快把孩子抱來給我瞧瞧。」歷史現場的實況不得而知,但若從古代漢醫的觀點,這個流程卻是「大誤」。
產婆此時須把孩子抱開,也不可透露嬰兒的性別,以免不合期待,讓母親心神受創。因為即使順利生下寶寶,這場生死馬拉松仍未到盡頭。血崩不止、胎盤未排出、惡露不盡,皆為重重險關,所以產後三日須密切注意產婦的性命安危,三日到七日也還在觀察期。直到確定沒有致命的病變,警報解除,便可開始滋補調護,不過也要到三十日後才能正常作息,就像現今熟悉的「坐月子」一樣。
陪伴產婦的「三姑六婆」
但生產一定有風險,若不幸遇上難產,除了用湯藥催生,醫書中還曾留下看產人「神之手」的紀錄。
由於產婦胎位不正,胎兒的手先產出,稍不慎便可能難產而亡。所幸產婆把胎兒推回產道,又按摩轉正胎位,最後終於平安順產。
類似的紀錄並不少見,古代希伯來文獻中就曾記載功力高超的產婆,以此接生難產雙胞胎。漢唐間的醫書也說,若胎兒手先伸出來,可將其推回重新生過。有意思的是,醫書指示推回之前,可在其掌心寫下父親的名字,威嚇一下,「讓逆子改邪歸正」!
「男性醫家強調的是父權感應,但從這個記載可推測,當時的助產者可能具有急救難產的臨床技術。」李貞德分析:「整個生產過程不會有醫者在旁,看產人其實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然而,醫書由男性撰寫、收錄、建立醫療知識系統,這一群默默提供產婦支持的助產女性,難登「大雅之堂」。漫長歷史中,她們只屬於傳統三姑六婆之一,沒有醫者之名,沒有話語權,卻可能是真正實踐、傳授產育知識的專業者,陪伴婦女度過生死難關。

溫柔生產,找回產婦醫療主體性
綜觀古人孕產歷程,與現在最大差別當屬「生產體位」,究竟女人為何從站立或半蹲,轉向平躺著生孩子?
李貞德分析,垂直體位是過往東西方普遍的分娩方式,轉向平躺式,大約在 18-19 世紀醫院制度興起後。
生產空間從熟悉的居家移往機構化,孕產主體由產婦轉向醫生,逐漸改變了婦女的生產經驗。
以醫生為運作主軸,婦女躺平成為更方便醫療處置的姿勢。透過現代醫療的幫助,許多高風險孕婦得以順利生寶寶,大幅降低難產喪命的機率。然而,高度醫療化的介入,也將生產與女性主體經驗隔絕開來,扭轉了以產婦為中心的分娩歷程。
長年關懷性別醫療史,李貞德經常受邀分享,在過去的時空,婦女曾有過多元的懷胎與生產經驗,產婦與助產者相互協力;被動躺著、由醫療者全權決定,並非恆常的標準答案。但她也提醒,這不是抗拒醫療、重回傳統的絕對二分法,而是透過史料爬梳,跨越到不同時空汲取經驗,看見多元的選擇可能。
「歷史就像一個巨型資料庫,透過認識不同時空的人類經驗,能幫助我們反思,瞭解到當下身處的環境和其中的現象,不一定是唯一選項。」李貞德娓娓道出多年研究的關切:「這不僅僅是研究生育史或女性史的關懷,也是歷史學作為人文學科很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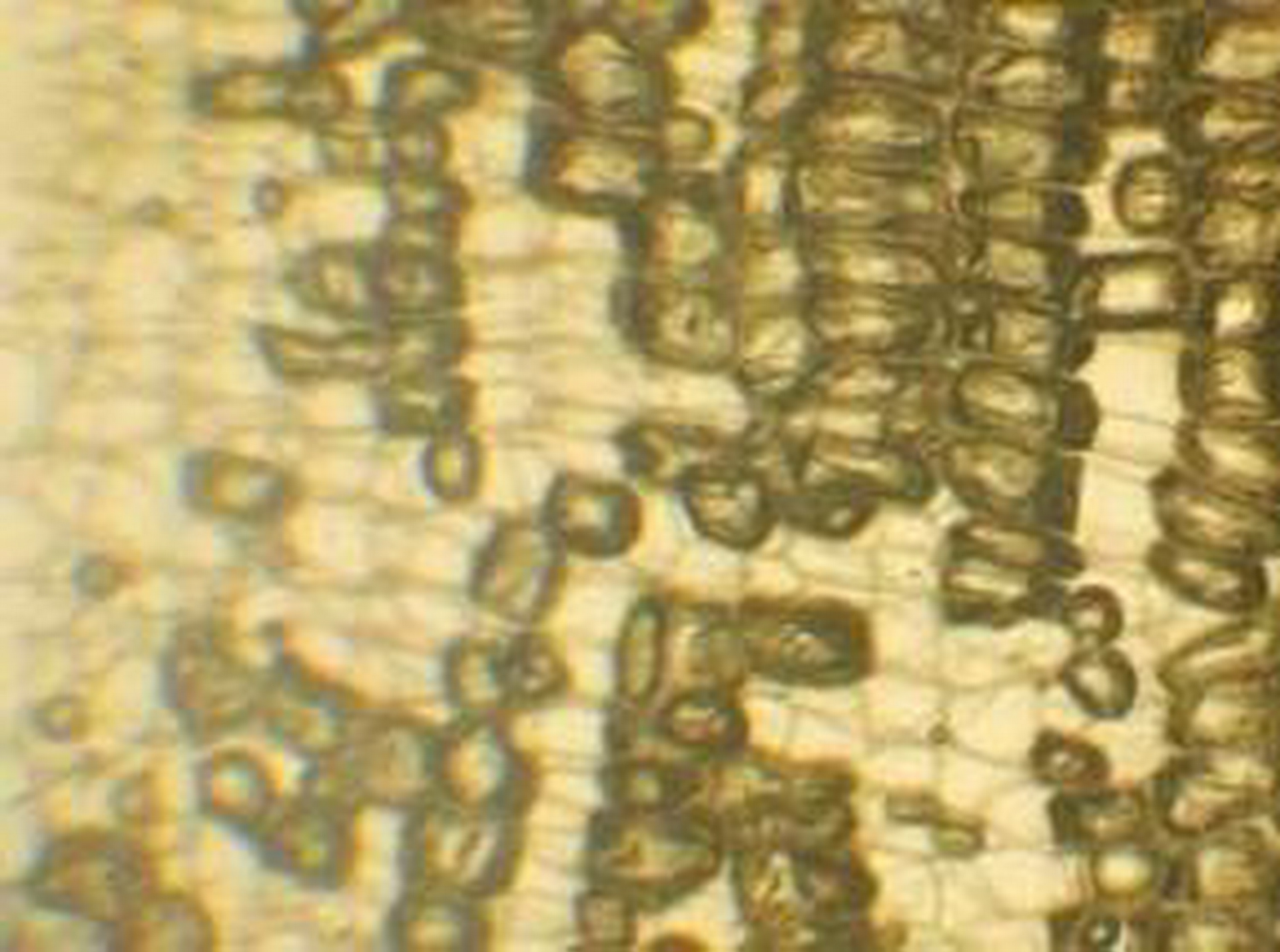











《運動基因》立體封面72dpi.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