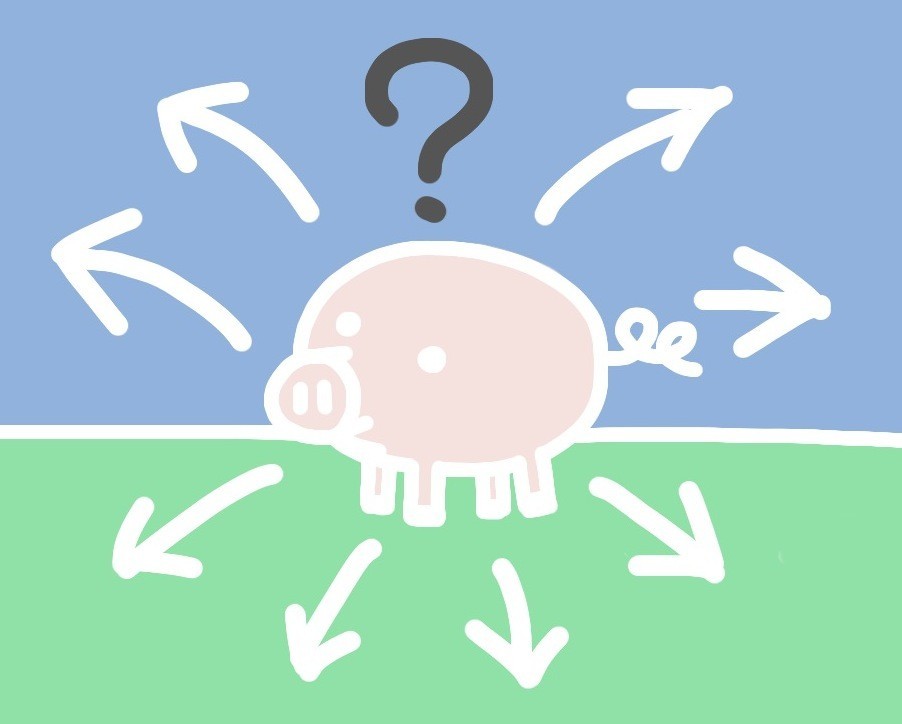
就英美分析哲學界而言,佛羅里達哲學系是目前自由意志和行動哲學(philosophy of action)領域排名第一的系所,由他們統籌這個計畫當之無愧。然而,這個顯然是關於人類行為機制的研究,為什麼是哲學家,而不是,例如說,心理學家或者神經科學家來負責策劃?(當然,這個計畫還是少不了科學家,畢竟我們不能期待空想就知道人有沒有自由意志。我忘了在哪看到的另一篇報導說這個計畫中有兩百八十萬將挹注和自由意志有關的經驗科學)
這或許就是一個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可以對經驗科學有貢獻的例子:科學家好奇人有沒有自由意志,因為人有沒有自由意志事關重大,可能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選擇和人生,也可能影響我們在不在乎自己對別人做了什麼事情。問題是,自由意志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人在不同的討論脈絡使用「自由意志」這個詞,可能是在說不一樣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可能只有其中一些(的某些部份!)跟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選擇和人生,以及我們是否在乎自己對別人做了什麼事情有關。
舉例而言,科學家發現在人意識到自己做的決定之前(幾百毫秒),大腦會先出現一種可以藉由儀器探測到的活動(readiness potential)。因此有人說人沒有自由意志,因為這個發現證明了你的決定不是你的意識(conscious)做的,是你的神經系統做的,你的意識只負責「回報」神經系統做好的決策。
姑且不論這個實驗能不能證明我們的意識真的只是神經系統的傳令兵(科學家們自己也有爭論),就算我們假設這件事情已經在科學上被證實,「人沒有自由意志」這個結論就可以因此被證成嗎?
「不一定,」聰明的你會說:「要看你說的『自由意志』是什麼」
沒錯。
我們當然相信如果一個人在行動選擇上受到某些限制(例如被催眠、被拿槍抵著腦袋),那麼他就不是自由的,也因此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全責,更無法好好地(在那個時候)經營自己的生命、掌控自己的選擇。然而,「被自己的神經系統限制」可以算是上面這種限制,或者至少算是跟上面這種限制同類的限制嗎?「被自己的神經系統限制」能成為一個人不為自己的行為受處罰的理由嗎?要是你「被自己的神經系統限制」,你就不再能夠認真面對自己的人生嗎?
囉唆地說,自由意志這個概念可能包含很多部份以及歧義:
A
B
C
D
:
:
其中有一些部份在科學實驗之下可能被證明不存在:
A → 不存在,因為人的決定是神經系統做的,意識只是個蠢記者
B → 不存在,因為量子力學是真的(換句話說,你的決定在某種意義上是隨機的)
C
D
:
:
但是這些被證明不存在的部份,卻不見得是支撐我們對於自由意志的重要期望和寄託的部份:
A → 不存在,因為人的決定是神經系統做的,意識只是個蠢記者
B → 不存在,因為量子力學是真的
C → 支持道德責任
D → 支持行為者對自己生命的掌握
:
:
要知道關於自由意志的科學實驗對於道德、法律以及你的人生有什麼重大影響,你得知道這些科學實驗支持和否定的是自由意志的哪些部份,以及這些部份對我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然而,你要怎麼知道這些事?至少你得搞清楚,當我們說「道德責任預設自由意志」以及「一個人能掌握自己的人生僅當他擁有自由意志」的時候,我們講的「自由意志」到底是指什麼。
這件事情沒辦法藉由經驗科學探究找到答案。科學家可以是我們的神經系統的專家,他們很清楚這些神經系統相關的詞彙指的到底是什麼,也可以告訴我們這些神經系統相關的詞彙指涉的機制到底存不存在,或者如何運作。但是就算科學家對於人的神經系統瞭若指掌,他也不見得能知道人到底有沒有自由意志,因為「自由意志」是一個模糊的日常概念,不是一個已經被準確定義的腦神經專有名詞。
我當然相信,如果人有自由意志,這個自由意志一定是奠基於人腦的某些機制(換句話說:自由意志有腦神經基礎和物理基礎,而不是源自於神蹟或魔法)。然而,在知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自由意志」到底是指什麼之前,我們沒辦法知道自由意志到底預設什麼樣的能力或性質。如果我們不知道自由意志預設什麼樣的能力或性質,我們就沒辦法知道自由意志到底預設什麼樣的腦神經基礎。而如果我們不知道自由意志預設什麼樣的腦神經基礎,就算我們完全了解人腦,也無法依據這樣的理解推論人有沒有自由意志。
換句話說,就算科學家已經建造出完整的理論,完全了解人腦的每一個部份以及它們的功能,他們也需要一座搭在(明確的)腦神經術語和(模糊歧義的)「自由意志」之間的橋,才能根據這些研究結果對自由意志做宣稱。(唔,如果「自由意志」因為歧義而事實上是好幾個概念,你就需要很多橋才能把這些「自由意志」都搞清楚)
而當我試圖釐清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意志」到底是指什麼,分析它的各個歧義,找出它們的完整定義,我就不是在做腦神經科學,而是分析哲學和概念分析了。
當然,這類例子無法證明分析哲學對於經驗科學本身有幫助,因為分析哲學並沒有幫助腦神經科學家把那些神經機制研究得更徹底,讓我們的科學理論更有內容。然而,分析哲學確實企圖以另外一種方式擴充科學理論:分析哲學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概念和科學理論之間築橋,如果他們成功了,科學理論不但可以告訴我們那些用科學詞彙組成的宣稱是真的還是假的,也可以告訴我們那些使用日常的重要詞彙組成的宣稱是真的還是假的。在分析哲學的幫助下,科學理論不但可以告訴我們人腦有哪些神經機制,還可望告訴我們人到底有沒有自由意志。
Note
- Hsin-Hao Yu在我的臉書張貼了有參考價值的評論︰「你這篇文章很不幸的例子舉得很不好。Templeton Foundation 不是正統的學術基金會。Templeton 很明顯的是有宗教目的的基金會,學術界檢討 Templeton 的文章很多,很容易找到資料。Templeton 的目的不是給學者研究自由意志,而是為宗教宣傳。你問這個計畫為什麼給哲學家總監?答案很簡單,因為 Mele 願意被收買。科學研究在美國多半是拿聯邦政府的科學預算 (NSF 或是 NIH)。要是這兩個機構給哲學家錢做研究,會讓你的文章有信服力得多。NSF 贊助各種研究,應該很容易找到贊助哲學家的例子。你舉的例子有反效果,因為它證明了哲學家跟科學家不能合作。如果可以的話為什麼哲學家要走旁門左道,要收 Templeton 的賄款?」如果他說的是真的,我提到的基金會研究計劃案就不能作為哲學家的貢獻受到科學認可的例子。然而,我相信Yu也會同意,這個用來開頭的例子好不好,跟文章中後的推論和介紹是否忠實無關。
本文修改自哲學哲學雞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