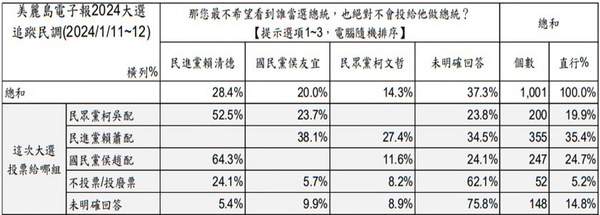一般人討論土壤生態系的成員時,往往會以微生物為主體;有的會研究土壤中甚為重要的環節動物--蚯蚓,或是土壤昆蟲,例如膜翅目的螞蟻、蜚蠊目的白蟻與部分土棲的蟑螂,以及一些鞘翅目和半翅目的土棲幼蟲等,還有其他的小型節肢動物,例如等足目的鼠婦;大型動物的部分,可能會想到鼩鼱目的鼴鼠,和一些會鑽地道的嚙齒目鼠類等等。鳥類與土壤生態系的關係則比較少人在討論。
其實有不少鳥類的生活史也和土壤有密切的關係,這包括了育雛階段穴居於土洞的鳥類,以及築巢會使用到土壤材料的鳥類。這些鳥類雖然只有某一階段會運用到土壤環境,卻是聯繫土壤生態系與其他陸域及水域生態系重要的一環。
掘土築巢:自己的家自己挖
翠鳥科(Alcedinidae)有不少物種都是掘穴築巢者,例如翠鳥和斑翡翠。翠鳥通常會選擇河岸邊陡直的土坡育雛,利用雨季沖刷掉邊坡植被、形成裸露土坡的時期挖洞營巢,育雛期間由雌雄鳥共同分擔孵卵的工作。近幾年在臺灣,由於水泥堤岸日益取代土堤,加上氣候變遷使得降雨頻率不規律,使得翠鳥可營巢的地方日趨減少。

與翠鳥科同樣屬於佛法僧目的蜂虎科鳥類,也會挖掘土洞或運用天然的樹洞與岩縫作為巢穴。蜂虎科鳥類的築巢方式與翠鳥相似,成群在河岸附近的砂質峭壁或水邊的土坡上掘穴築巢,挖洞由雌雄鳥輪流進行。
蜂虎有時會集體營巢(colonial breeding),有時則單獨營巢(solitary breeding)。

燕科(Hirundinidae)鳥類有大半的鳥巢巢材都與土壤相關。一些早期發展的燕科鳥類,例如棕沙燕、灰沙燕等物種,也會以掘穴為營巢的方式。
棕沙燕的繁殖期在三到七月期間,營巢方式與翠鳥相似,但是牠們的生活群聚性很高,會成群在河岸的砂質峭壁或土坡上掘洞築巢,挖洞也是由雌雄鳥輪流進行。
以燕科和蜂虎科鳥類的集體掘穴聚落來說,牠們群聚的巢窩其實是很類似人類的社區一般。集體繁殖對這些鳥類的好處很多,包括增強對於入侵者的偵查、彼此守望相助以加強巢位上的防衛;群體覓食也能增加覓食效率,並提高幼鳥存活率。

興土木的鳥界有巢氏
燕科鳥類築巢能力較為演進的物種則是一些泥巢鳥(mud nest birds),牠們有辦法以濕泥、乾草等素材混合唾液來塑造碗狀泥巢(例如家燕、洋燕等)。其中築巢最極致者,還能製造封閉型的泥巢(例如赤腰燕和美國的崖燕)。牠們的泥巢相當的精緻,除了穩固的外巢結構,還提供幼雛穩固又柔軟的嬰兒床。以赤腰燕舉例,用泥丸砌好巢形後,通常還要花上一週以上的時間來鋪設巢內環境,且經常使用從其他地方撿拾來的羽毛。
由於泥巢鳥通常會運用土壤作為巢的接著劑,或直接以土壤作為巢窩主要的塑形結構體,因此不同的燕子,對於土壤的選擇其實會有一些不同。不同的燕科鳥類,對泥巢修補上的土壤採集也會有不同的情形。
Delbert等人在1970年代的研究曾發現美國的崖燕和家燕在建造鳥巢時,崖燕所選擇的泥土(mud)相較於家燕有較高的砂粒含量與較低的坋粒含量。高砂量的土壤很可能有利於改善崖燕在築巢進行操作與塑形時的容易度。在土壤有機質的部分,家燕的巢喜歡參入一些草莖、馬鬃與羽毛等較大的物質,而崖燕巢則含有少量的種子與其他細粒物質。崖燕的巢看起來就像好幾個曲頸瓶聚集在一起,對崖燕來說牠們可能想要排除掉一些笨重龐大的材料物質,然而對家燕而言那些粗大的草莖卻是用來綑綁土塊的好材料。
自然界當中還有一些鳥類也善於使用泥土來作築巢材料,像是澳洲的灰鴕鷚(Struthidea cinerea)、鵲鷚(Grallina cyanoleuca),都是以能在樹枝上建造碗型泥巢而著稱的鳥類。

有些鳥類十分喜愛複雜的土洞、但自己不會修築,因此採取和其他物種合作的方式,像是穴鴞(Athene cunicularia)就依賴草原犬鼠淘汰的舊巢穴,牠們則負責幫草原犬鼠協防抵禦較大的掠食者。穴鴞還很喜歡收集牛糞來作為巢穴的填塗材料,牛糞不僅可以調節巢穴的微氣候,還能用來吸引昆蟲的聚集,便於直接在自家門口覓食,有利於哺育幼兒。
紐西蘭的大斑幾維鳥(又稱為大斑鷸鴕,Apteryx haastii),平時喜歡待在巢穴當中。通常巢穴挖成之後會先讓苔蘚與雜草生長覆蓋幾個星期後才進駐,讓偽裝作得更好。牠們甚至還會開挖數十到一百個洞穴作為躲藏之用,且每天都會改變棲息的洞穴。並且通常在夜間才會出來活動捕食各類底棲昆蟲和小型動物。

自然界有一些天然土洞或岩洞也是很多鳥類喜歡進駐棲息的居所,像油鴟(Steatornis caripensis)、金絲燕屬(Aerodramus)的鳥類或是一些貓頭鷹等等。油鴟和金絲燕為了應對洞穴中的活動,還會使用類似蝙蝠的回聲定位法;不過牠們用來回聲定位的聲音是我們耳朵可聽得到的頻率;油鴟的聲音非常吵雜,加上牠們喜歡群聚,國外曾有電視節目錄製了牠們在洞穴當中可怕的吵雜聲響。
這些依土而居的鳥類其實在自然界的生態當中也有著很多有趣的事物。
參考資料
- 王怡平、袁孝維。金門栗喉蜂虎營巢地及生殖族群變遷監測。國家公園學報 15(2):31-41, 2005。
- 袁孝維、王力平、丁宗蘇。金門島栗喉蜂虎(Merops philipennus)繁殖生物學研究。國家公園學報 13(2): 71-84, 2003。
- 劉小如、丁宗蘇、方偉宏、林文宏、蔡牧起、顏重威。台灣鳥類誌第二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重返台灣河川 小小翠鳥要成家(環境資訊中心)
- DELBERT L. KILGORE, JR. AND KATHY L. KNUDSEN. ANALYSIS OF MATERIALS IN CLIFF AND BARN SWALLOW NESTS: RELATIONSHIP BETWEEN MUD SELECTION AND NEST ARCHITECTURE. DEPT. OF ZOOLOGY, UNIV. OF MONTANA, MISSOULA 59801. ACCEPTED 1 AUG. 1976.
- Great spotted kiwi (Apteryx haastii)(ARKive)
- Signe Brinklov, M. Brock Fenton, and John M. Ratcliffe. Echolocation in Oilbirds and swiftlets. Front Physiol. 2013; 4: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