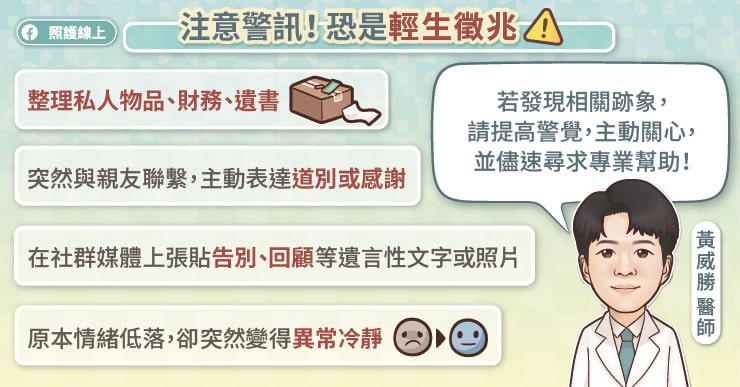編註:本文目的為介紹關於憂鬱症的藥物治療研究進展,然 K 他命並非現行常規治療,不當使用對身心或將造成傷害,請務必注意。

文/王俸鋼|彰基司法精神醫學中心主任,專長:司法精神醫學、犯罪學
憂鬱症一直是精神醫療相當關注的疾病, 2007年知名醫學期刊《刺胳針》(Lancet)中,即有研究使用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計算各種疾病佔人類社會失能負擔的比例,如癌症佔11%、呼吸系統疾病佔8%…等。而神經精神類疾病佔所有疾病的28%,其中光是憂鬱症一項,就佔了全數身心疾病於人類失能負擔的10%。
可以想像,若人類能完全克服憂鬱症,將會有效增加人類社會的動能。在社會長期的努力後,大眾已較能接受憂鬱症的存在,也了解這個疾病需要妥善的治療。
但是憂鬱症治療一直以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雖然目前現代醫學的治療模式,號稱從生物、心理、社會多管齊下恢復患者的健康,但由於藥物所提供的生物治療較快速且方便,因此台灣多數憂鬱症患者到了醫療院所,幾乎無可避免使用藥物當作重要治療方式。
然而現今的治療方式,也並未讓醫界、患者感到滿意。除了藥物治療,不管在使用不同藥物、或者採取合併、加強藥物療效的各種策略下,還是有一定比例的患者會無法達到足夠的反應;而這將近三分之一的患者,被稱為難治型憂鬱症,他們會因為治療效果不佳,長期處在憂鬱情緒中,合併著各種身體不適症狀,幾乎喪失原本功能卻得不到親友諒解,在這社會上辛苦的活著。很多時候這種絕望到達極限時,用自殺來結束這種痛苦的生命,也是這類患者常常會選擇的絕路。即使幸運能夠成為那三分之二對現行治療會有反應的患者,現行的抗憂鬱劑仍有著見效速度不夠快(往往需要4到6週才能出現效果)、症狀不見得能完全改善的缺點。
從二十世紀中出現第一個抗憂鬱劑開始,經過近半世紀的醫學發展,藥物的治療原理上並沒有多大的改變。直到二十一世紀初,這個狀況竟然出現了有趣的意外轉機。
低劑量K他命 高效治療憂鬱症
K他命(ketamine),一種NMDA受體拮抗劑,原本是一個常用的短效麻醉劑,這幾年來成為台灣最惡名昭彰的三級毒品,從2006年來就爬升為警方查緝最常見的非法濫用物質,2010年佔所有查獲非法物質的74%,也是19歲以下青少年最常用的毒品。到了2012年底,在立法院至少有8次討論要將K他命升級為二級毒品以加強管制,足見其引起的社會恐慌。
但是在2000年,就有小規模的雙盲隨機人體實驗,發現靜脈注射小劑量的K他命,似乎確實有相當明顯而快速的抗憂鬱的作用。而且那個快速是在幾小時之內就可以出現,相較於抗鬱劑需要數週的時間,相差真是不可以道里計。
到了2006年,更有針對難治型憂鬱症患者的人體實驗,發現K他命對這類憂鬱一樣有效,靜脈注射後2小時內就出現了明顯的抗憂鬱效果。而這樣的實驗結果,用在俗稱躁鬱症的難治型雙極性憂鬱,治療效果一樣明顯。一項2010年的實驗顯示,這種每公斤人體給予0.5毫克的低劑量(用在麻醉時,每公斤需2毫克),對這種難治型的雙極性憂鬱,原本無法對傳統藥物治療出現效果的病患,有超過7成的患者出現了療效。而且憂鬱分數改變超過50%的速度,在用藥後平均40分鐘就出現了。更重要的是,這種抗憂鬱效果並非來自毒品帶來的欣快感,因為K他命的抗憂鬱效果,在用藥後平均能夠維持6.8天,甚至其中四分之一的受試者,抗憂鬱的效果維持超過了兩個星期以上。
由於這十年多以來的實驗和觀察,醫學界幾乎可以確認K他命在治療憂鬱上所帶來的效果,完全不同於傳統抗憂鬱藥物的表現,2012年相當具有權威及歷史的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發表了一篇回顧文獻,探討了K他命所帶來的憂鬱症治療效果的可能解釋,並認為可能與神經細胞的突觸生成(synaptogenesis)有高度的相關。
文章的作者之一,美國耶魯大學精神科名譽教授Dr. Dunham甚至告訴網路媒體,認為K他命對憂鬱症治療的發現很可能是這半世紀來憂鬱症治療的最大突破。事實上,有研究者在2014年還陸續發表了K他命對改善自殺意念、治療強迫症、甚至是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都有明顯快速而有效的反應。

從實驗室到診療室 K他命療法的利與弊
然而在臨床實際應用上,K他命有著無法被忽視的缺點。除了它潛在的濫用及成癮性、各種急慢性的身體副作用(如現今常被廣為宣傳的膀胱炎),它也很常讓患者在使用後(往往是1個小時),會出現幻覺和解離感。況且目前多數臨床研究的使用方法,雖然都是用相對低劑量,但多半需要花1~2小時慢慢的以點滴注射,每週二到三次的頻率在做治療,而這種治療方式,在一般臨床的設置情形下,還是相當的不方便。
而且目前醫學界對K他命的治療,雖然觀察到明確而快速的療效,但是在它真正的藥理機轉上,仍然是處於假說的階段;這方面台灣的研究也受到了國際相當的注意,因為台灣的團隊曾用與K他命在藥理機轉上完全相反的藥物,做為憂鬱症治療的嘗試,結果一樣出現的療效!
這樣的發現其實也並不令醫界意外。目前廣為使用的抗憂鬱藥物中的一類,是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SSRI),但較少為人所知的是,在歐洲有一種也被實驗承認具有抗憂鬱效果的藥物,它的作用機轉,是某種血清素再回收的「促進劑」,這兩類完全相反的機轉,都有抗憂鬱的效果。
因此雖然目前美國的臨床醫師,已經在這一、兩年逐漸企圖在患者知情同意的狀況下,「適應症外」(off label)讓難治型的憂鬱症患者使用K他命做治療,但整體而言,因為有難以處理的副作用,正式的治療指引仍未採用這種療法。
更安全有效的K他命療法?
不過醫學的努力從未停止。2013年美國麻醉學會的年會上,就有研究者試圖用抽血驗血中代謝物的方式,來看能不能分辨出哪一些患者對K他命可能有反應,而哪些患者可能沒有,用這樣的方式來提前預測是否能用抽血的方式,來給真正需要的患者開立K他命。也有其它的研究,將K他命做成鼻噴劑,並研究治療的反應,發現和靜脈注射可能一樣的有效,而且副作用更少。
而今年(2014)6月的研究最令人指奮的是,有研究者發現,K他命的代謝物——水氧正k他命(Hydroxynorketamine),在治療憂鬱上與K他命一樣的快速、有效的表現,而且因細胞受器作用的不同,不會出現K他命的複雜副作用。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憂鬱症的治療會有驚人的突破,我們即將擁有對單極、雙極憂鬱都有治療效果的新藥,能在數小時之內出現療效、且治療反應更好,降低憂鬱症病患自殺意念並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質。
而這一切的來源,卻是一個易遭濫用而令社會頭痛的麻醉藥品。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說的也不外如是。
參考資料
- Prince, Martin, et al.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The lancet 370.9590 (2007): 859-877.
- Duman, Ronald S., and George K. Aghajanian. “Synaptic dysfunction in depression: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Science 338.6103 (2012): 68-72.
- Berman, Robert M., et al.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ketamine in depressed patients.” Biological psychiatry 47.4 (2000): 351-354.
- Zarate, Carlos A., 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of an N-methyl-D-aspartate antagonist in treatment-resistant major depress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3.8 (2006): 856-864.
- Rasmussen, Keith G., et al. “Serial infusions of low-dose ketamine for maj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Psychopharmacology (2013): 0269881113478283.
- Murrough, James W., et al. “Antidepressant efficacy of ketamine in treatment-resistant major depression: a two-sit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0.10 (2013): 1134-1142.
- Huang, Chih-Chia, et al. “Inhibition of glycine transporter-I as a novel mechanism for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Biological psychiatry 74.10 (2013): 734-741.
- Lapidus, Kyle AB, 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Intranasal Ketamine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14).
- Feder, Adriana, et al. “Efficacy of Intravenous Ketamine for Treatment of Chroni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psychiatry (2014).
- Hsu, Liang-Yin. “Ketamine use in Taiwan: Moral Panic, Civilizing Processe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2014).
- Paul, Rajib K., et al. “(R, S)-Ketamine Metabolites (R, S)-norketamine and (2S, 6S)-hydroxynorketamine Increase the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Function.” Anesthesiology 121.1 (2014): 149-159.
- Ballard, Elizabeth D., et al. “Improvement in suicidal ideation after ketamine infusion: Relationship to reductions i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