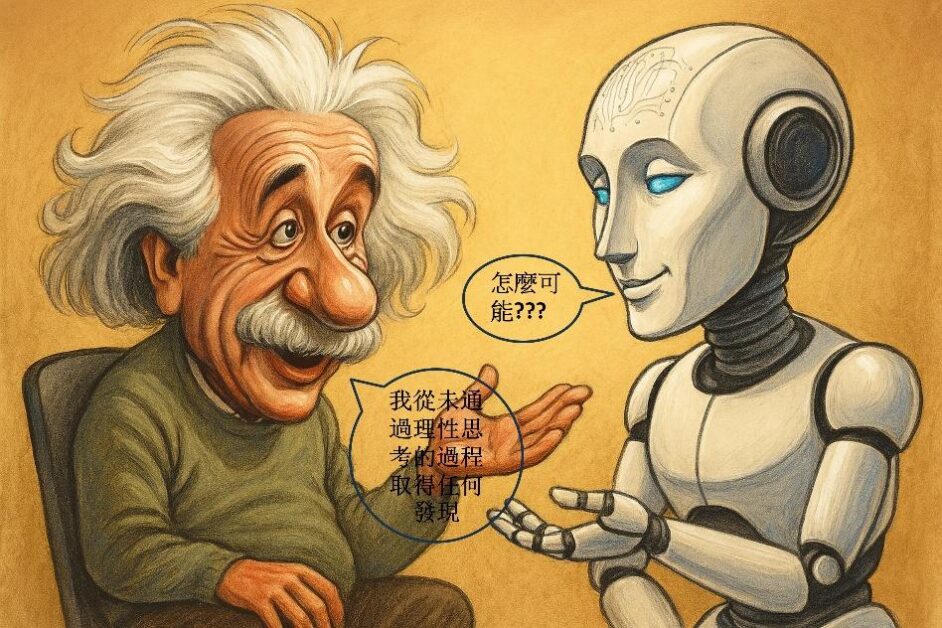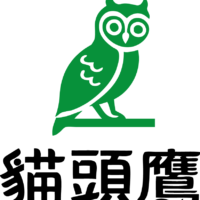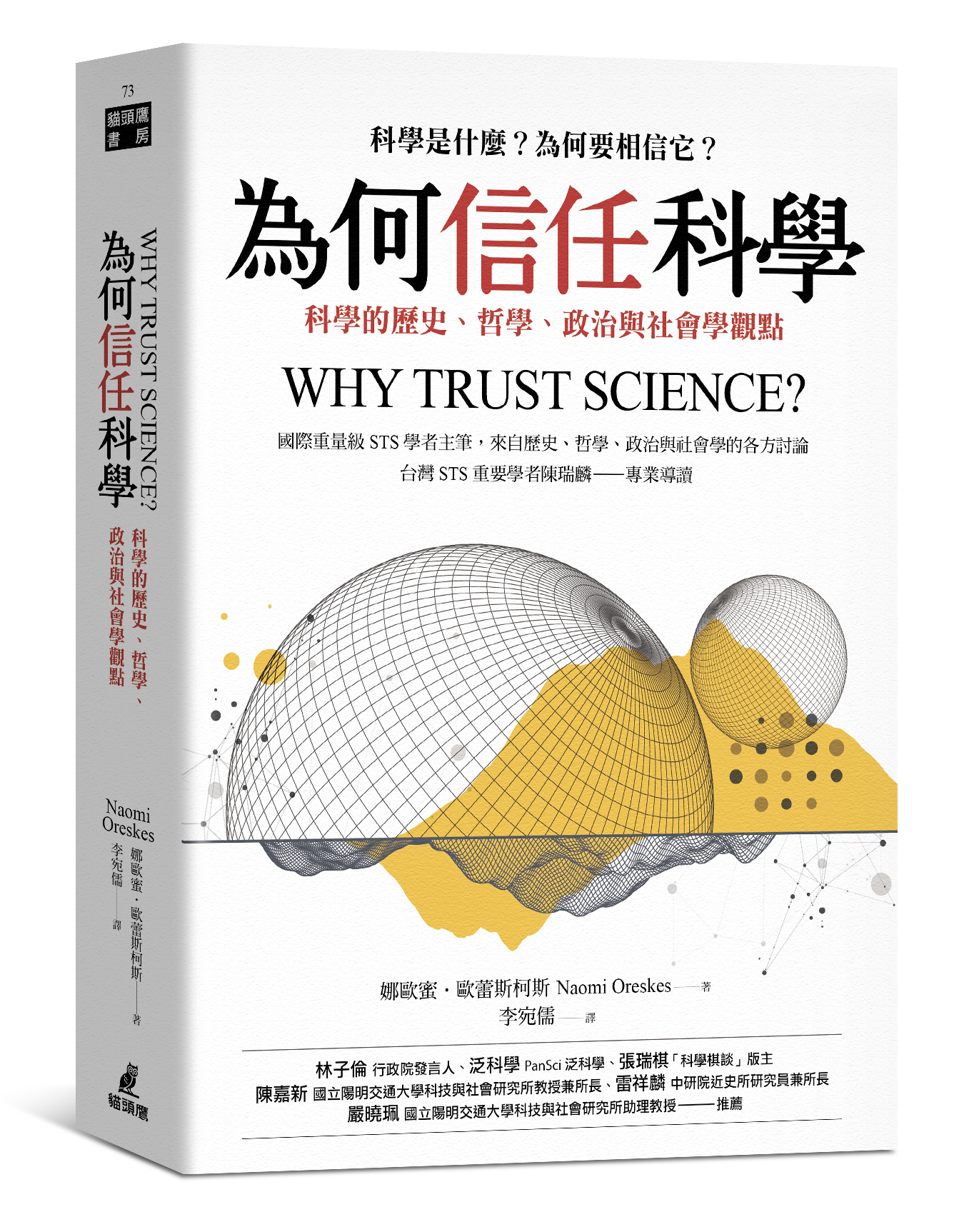作者:伊恩‧塔克(Ian Tucker)
本文原始連結:Science writing: how do you make complex issues accessible and readable?
譯者: 黃敏芳(畢業於陽明大學醫放系、陽明大學醫工所及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ism)
在英國倫敦的皇家學會準備要頒發年度圖書大獎的前夕,我們邀請五名頂尖的作家來談談,在這個充滿科技思想的年代,什麼是好的科學寫作?這五名作家分別是: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詹姆斯‧葛雷易克(James Gleick)、布萊恩‧格林恩(Brian Greene)、瀧‧法蘭克(Lone Frank)和喬許.佛爾(Joshua Foer)。
上個月月底,五名世界上最頂尖的科學作家齊聚在英國倫敦,等待英國皇家學會頒發2012年科學書籍獎(Winton Prize for science books)。在晚上頒獎之前,我們把這五名作家找到皇家學會圖書室來,聊聊報導詹姆斯.葛雷易克所謂的「我能夠理解的部分」(very edge of what I’m able to understand)到底是什麼。
像葛雷易克這樣的作家在我們瞭解世界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隨著科學發現越來越多的宇宙奧秘,科學理論和科學發現也變得越來越技術性、越來越以資料為導向。
因此,在將複雜的科學研究變成平易近人、具有啟發性質的散文過程中,科學家和科學作家所扮演的角色變得很微妙、也很重要,就如同聚集在此的五位作家所扮演的角色一樣。這個獎項的第六位候選人,《病毒風暴》(The Viral Storm)一書的作者,納森.沃爾夫(Nathan Wolfe)無法參加這場討論,因為他人在剛果的叢林中。不過頒獎的時候不需要即時衛星連線,因為裁判將獎項頒給葛雷易克的書《資訊:一段歷史、一個理論、一股洪流 》(The Information)。
為什麼科普報導很重要?
喬許.佛爾:英國皇家協會於1660年成立的時候,當時那些受過教育、多才多藝的人還是有可能真正瞭解世界萬物的道理。不過現在辦不到了。史迪芬.平克或許是偉大的認知科學家,不過我賭他沒辦法解釋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是怎麼被發現的。
布萊恩‧格林恩:他剛剛才解釋給我聽,而且解釋得還不錯。
喬許.佛爾:那表明為什麼我們越來越需要偉大的解釋者(interpreter)。我們這些人變得越來越重要是因為科學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以致於需要其他人來協助我們瞭解科學。
當你寫作的時候,你怎麼處理困難的部分?你希望讀者一口氣看完你的書,還是希望讀者努力挖掘埋藏在每一行裡面的真知灼見?
史迪芬.平克:在提筆撰寫我的第一本認知科學書籍之前,我從一位編輯那邊得到大概是我收過最好的建議。她說,很多科學家和學者在為各式各樣的讀者寫作時,有一個共通的毛病:他們採取了紆尊降貴的態度寫作。他們假設目標讀者不怎麼聰明,可能就是一些卡車司機、貧苦農民和編織娃娃的老奶奶,所以他們寫作的語氣就好像在跟小孩說話一樣,態度高人一等。她說:「你應該假設你的讀者跟你一樣聰明、好奇。因為他們不瞭解你知道的事情,所以你才會在這邊把那些他們所不知道的事傳達給他們。」只要我提供給讀者瞭解一個概念的所有必須材料,我願意讓他們做點事。
布萊恩‧格林恩:理想的狀況就是,讀者可以從不同的層面來讀一本書。如果他們為了瞭解所有東西,所以真的很想挖掘書中的訊息,包括附錄在內,希望神會保佑他們,因為那真是太棒了!不過對於那些只想要深思熟慮重點部分的讀者,我希望書中文字有足夠的動力可以推動他們完成思考的過程。要取得平衡很難,不過我想當你終於靠近目標的時候,人們會感謝你。
瀧‧法蘭克:很多人會說,不要使用艱難的專有名詞。不過如果你可以在寫作的時候好好運用白話文的技巧,基本上你可以解釋所有的東西。
有誰曾覺得某個東西太難解釋而把它省略掉?
布萊恩‧格林恩:幹過這種事嗎?我老是在做。原則上我同意你可以解釋所有的東西,不過你試過用代數幾何來向一般人解釋對稱嗎?祝你好運啊。有些事情真的很難,沒有受過技術方面的訓練很難瞭解。不過即使省略一些東西,還是要保留精華,這樣主題的核心就有很多部分可以發揮,讓你可以好好表現。
喬許.佛爾:到頭來,每個在這個房間裡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個娛樂大眾的人。我們對抗部落格、電動和電影,努力爭取讀者的注意力。我試著講述能讓人們從甲地到乙地的故事,我不是指故事要有頭有尾,而是指讓他們可以瞭解某個主題。被帶進像這樣的知識之旅,報酬可是很豐厚的。
詹姆斯.葛雷易克:我不知道這算是懺悔還是吹牛,不過我常常遇到我能夠獨立搞清楚的事。我寫書的主題就是我會關心的事,我講的故事就是我覺得跟我們文化有關的東西,而我們的文化越來越跟科學性的東西有關。我的書《資訊:一段歷史、一個理論、一股洪流 》在某方面看來並不是一本科學書籍。不過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必須處理技術性的東西。所以對我來說,要理解這些技術性的東西常常得問聰明的人很多笨問題。
一般大眾可能無法瞭解科學寫作的特點,而把科學寫作跟其他的非文學類混淆在一起。
詹姆斯.葛雷易克:我屬於一般大眾。我不覺得我在這邊具有代表性。除了喬許.佛爾以外,在場的人都是或曾是科學家。我進這一行是因為新聞的關係。我從來沒想過要成為科學作家。我抗拒成為科學作家這種想法。
瀧‧法蘭克:我同意。我覺得很多時候,區別科學寫作跟非文學類的標準相當無聊、刻板 。
史迪芬.平克:隨著科學的思考邏輯運用到其他領域,科學寫作和非文學類之間的差別會越來越難區別。以我的書《人類天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為例,這本書混合了歷史、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而且這本書還被提名角逐歷史類獎項。我觀察歷史的走向,而就我個人的看法,如果你提到走向並且使用諸如增加或減少這種字眼,就要有數據佐證。所以我所報導的是可以被量化、可以用圖表做總結的歷史。不是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是這樣做歷史研究。就這兩者的範圍看來,科學和一般性非文學類書籍之間的區別正在崩壞。假如有人想要用我的方法來解釋歷史現象,就表示不能只是認為歷史事件只是接二連三發生,而是要思考為什麼這些事件看起來是往某個方向走。如果你觀察到一個現象,想要使用比較一般性、簡單的詞彙來解釋,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你就是在做科學。
就很多人看來,學習跟困難息息相關。你覺得有時候學習就是要很困難,這樣才會被認為是科學嗎?
史迪芬.平克: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或許可以讓你瞭解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的想法哪裡不同。有次我參加某個跨領域研討會,與會者有科學家和人文教授。在某場探討繪畫的演講結束時,演講者說:「好吧,我希望我已經從不同的角度讓這個主題更複雜。」我那時候想,這就是科學家和評論家之間的差別。科學家會說:「我希望我已經從不同的角度來簡化這個主題。」
瀧‧法蘭克:現在很多讀者期待每件事都應該要更簡單,不應該處理每件事,所以如果一本書有點難,人們就不會去讀它;人們會把它丟掉,然後找其他的書來看。
詹姆斯.葛雷易克:那真是令人沮喪的想法。我希望這不是真的。如果這是真的,我就不寫作了。我覺得大家喜歡接受挑戰,而且你不一定要拿科學類書籍來挑戰他們,你可以用歷史書或是傳記文學。當你翻開一本書來讀,不管你讀多少,你讀就是因為你想讀它。
瀧‧法蘭克:我想你講的是1%,而不是99%的人。
詹姆斯.葛雷易克:你知道的,在出版業就是要爭取這些1%的人。
布萊恩‧格林恩:1%就可以賣很多本,在美國就可以賣三百萬本。
瀧‧法蘭克:我想這或許跟文化差異有關。我來自丹麥,科學在那邊不怎麼受到重視,幾乎沒有任何科學寫作。舉例來說,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最新的書沒辦法翻譯成丹麥文,因為沒有市場。你應該有感覺了吧。
現在科學書籍似乎有點在蓬勃發展,有人想猜猜可能的原因嗎?
布萊恩‧格林恩:謝天謝地,我的經驗跟你描述的丹麥狀況非常不一樣,丹麥的狀況太恐怖了。雖然我遇過的人不能代表全部的人,不過我覺得越來越多人真的想要瞭解科學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史迪芬.平克:真的越來越多。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住在一個用科學描繪一切的世界。人們不相信世界是5000年前被創造出來,至少那些我們試著吸引來買書的人不相信這回事。受過教育的人會接受我們是從靈長類演化而來;我們的心智要靠大腦的運作,所以我們會受到幻覺、謬誤和偏見的支配。正是科學提出這些存在已久的問題,並加以回答。
詹姆斯.葛雷易克:你剛剛說某個美國政黨沒受過教育!
史迪芬.平克:對啊,沒錯。
詹姆斯.葛雷易克:你提到的現象對我來說再明白不過了,不需要特別提出來問。我們當然關心科學,我們知道科學能夠解釋我們最想要找出答案的問題。我們國家裡的對立潮流(我們四個人住的地方)是最恐怖的事。就我看來,突然之間越來越多人不認為科學能夠回答這些問題。以前我沒看過這種事。當年我開始寫些有關科學的東西時,我從來不覺得這些事會有爭議性。
史迪芬.平克:可能因為在美國,某個政黨看起來非常反對世界科學觀。不過我覺得,他們的行為不能被認定是討厭科學,因為他們還是會在尋找石油的時候使用我們所相信的地球年齡作為依據。當他們生病的時候會去看醫生,而且他們跟我們一樣也會煩惱病菌演化產生抗藥性。他們不是阿米許人(Amish,基督教的分支教派,因拒絕採用現代科技而聞名),不是用古代的方式生活。所以就某種意義來說,他們已經融入科學的世界,只是在某些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界定道德與政治角色的議題上,他們會非常明確表達自己的立場,所以我覺得這跟完全不瞭解科學是兩碼子事。事實上,我們(哈佛大學)系上有個研究生曾做過一項實驗,結果顯示贊同和反對演化論的人,對演化論的瞭解其實差不多。我們不應該將少數熱門議題的說教行動跟針對整體科學世界觀的敵意搞混在一起。
你怎麼論斷一本書是否成功?銷售量?來自學術界的反應?
布萊恩‧格林恩:這些都是判斷的依據,不過我個人會捫心自問,如果換成是20年前,沒有人可以寄電子郵件給我的時候,我會寫這個題目嗎?當一個八歲的小孩寫信問我問題,而且表達出對於那些觀念的雀躍,他的行為跟銷售量或是支配性的影響都沒有關係。當有人很喜歡你的書時,你會覺得真好。
喬許.佛爾:如果不是這三個人寫出讓我在高中時深受影響的書(葛雷易克的《混沌》、平克的《語言本能》以及格林恩的《優雅的宇宙》),我想我不會坐在這裡。我在高中時期讀過的書影響我對世界的想法,以及我這輩子的志願。我想當你在思考如何評斷一本書是否成功的時候,沒有想過有時候得等上好幾年,才會知道一本書怎麼影響他人。
佛爾和法蘭克,你們兩個寫書的時候都把自己的經驗跟科學交織在一起。用這種方法寫書,會使你擔心處理主題的時候比較不客觀嗎?
瀧‧法蘭克:在寫一本有關個人基因體學的書時,很難跳脫出來用第三人稱發問:「你得到這些資訊時覺得怎樣?」你可能也會自己去找出這些資訊。我的經驗只是個案,針對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處理辦法。所以我不過是把自己當作實驗材料,從各個角度來敘述故事。這也是讓其他人感興趣的辦法。他們喜歡從個人故事中學習科學的知識。
喬許.佛爾:到目前為止,在探索那些我有興趣、而且想要找出解答的問題時,
我覺得寫作是個很好的工具。我不應該出現在我的書內,但是有時候書的主題太吸引我,使得我不可能從局外人的角度來講述故事。所以成為主角之一算是個蠻愉快的意外。我沒有辦法想像自己不投入的話怎麼去寫第二本書。
格林恩和平克,你們會以第一人稱來寫書嗎?
史迪芬.平克:我用第一人稱寫過一些散文,內容是有關幾年前我拿自己的基因體去定序的事。我可以想像寫一本書來討論使用第一人稱敘述人生大小事會遇到的困難,然後加入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像是人類會挑對自己有利的部分來講,還有記憶扭曲的狀況。
布萊恩‧格林恩:《優雅的宇宙》中有幾個章節就是以第一人稱寫成。當初的草稿沒有使用第一人稱,因為我顧慮到這麼做可能會讓人覺得我很自私,在一本寫給大眾的書裡面提到自己的成就。所以第一版的草稿裡面沒有放名字,只有一些想法而已,整個就是很糟。所以我重新修改,把該放的東西都放進去,像是誰做了什麼事,有什麼爭論,討論出來的解決辦法是什麼等等。然後,當我開始處理自己的成果時,整件事就變得自然了起來。既然我本來就參與在其中,那我就用第一人稱的角度來描述。這本書不用說故事的方法就沒辦法進行下去。
來談談譬喻。使用可以理解但是不完美的譬喻,以及使用可能無法令人理解的方式詳述一件事,這兩者之中前者比後者好嗎?
史迪芬.平克:譬喻是非常強大的。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辯稱,我們瞭解世界萬物,只是必須透過譬喻的方法來瞭解實際上的世界。我們的語言幾乎充滿了隱喻。不過文學性隱喻跟科學譬喻並不相同。在文學隱喻的世界中,隱喻和事物之間的連結越多,這個隱喻就越豐富美好。但是在科學譬喻的世界中,譬喻跟事物之間的連結越多,這個譬喻就越不好。譬喻必須慎選,解釋譬喻的時候要小心。你必須指明讀者相似之處為何,以及你用譬喻所解釋的東西跟譬喻之間的關係點是什麼。有時候可能會太專注於反覆衡量各種譬喻,使得你不知道哪一點真的有用,這就是可能會讓譬喻誤導人的地方。
我在某處讀到,譬喻就像是不合身的外套,最重要的部分蓋住了,可是某些地方會突出來,某些地方又限制你的活動。
詹姆斯.葛雷易克:我才不信這套說法!什麼事都有可能被做爛。不過我也相信譬喻是人類學習和探索世界的方法。物理學家聲稱大自然的語言是數學,而這說法多少有幾分真實性。不過我也相信,任何用自己的方法來理解世界的物理學家其實就是自動用譬喻的方式來思考。我相信,所有的科學模型或理論本身就是一種譬喻,雖然不是很完美,定義漏洞百出又不完整。但它就是個模型,不是世界本身。
在場有人試過寫小說嗎?
史迪芬.平克:我的另一半就是小說家,所以我深知自己的不足。
布萊恩‧格林恩:我出版過短篇故事,而且內容真的有科學成分。那篇故事跟時間旅行有關。這是我做過最有趣的事之一。故事在虛構的層面有一定的自由度,而事實的部分則跟真實的科學緊密相連,給故事一種安定性,害我必須小心分辨我是不是連事實的部分都用捏造的。
科學作家寫的是尖端知識還是幻想?
瀧‧法蘭克:很多人不瞭解,科學真的會影響人類思考的方法。他們以為文化來自哲學、戲劇和其他東西,而科學只負責製造裝置。我真的想讓人們看看,我們從科學得到的知識怎麼改變我們的文化。
布萊恩‧格林恩:我覺得讓小孩瞭解科學需要創意以及所謂的創意管教(creative discipline)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詹姆斯.葛雷易克:如果我們這些人都以為科學過程就是機械化又無聊,我不相信在場的人會寫跟科學有關的東西。我們五個人都很重視想像力和創造力,我們不是把這些元素當作偶然出現在科學過程中的意外,而是作為讓科學前進、使人感到興奮的要素。
史迪芬.平克:唯一的但書就是,在科學領域中,光只有想像力和創造力還不夠,正確性是不可或缺的。歷史上有很多充滿想像力的人被遺忘,因為他們那美好簡鍊的計畫跟現實搭不起來。
科學家撰寫學術期刊論文的正式、技術性作法會影響科普寫作嗎?
布萊恩‧格林恩:當我查閱某些1920年代的量子力學論文時,發現其中有一篇提到發生在實驗室裡的意外。撰寫那篇論文的科學家描述玻璃管炸裂的時候,一個硬幣被染污了,以及他加熱那個硬幣試圖去除污漬的過程。他在這篇技術性文章裡面完整講述了這個故事。現在的話很少看到這樣的事。因為我還沒進行全面性的研究,所以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個少見的例子,不過大家撰寫學術論文的時候,好像已經從講述某種發現的故事變成採用比較照本宣科的方式?
史迪芬.平克:我覺得真的是這樣,我想這都已經都被記錄下來了。相較於講述事情發生的過程,這在科學上就是個問題。問題出在,當你在期刊編輯的壓力下講述導到結論的故事時,將所有不成功的部分和意外按下不表,這種作為事實上就是在扭曲故事本身,因為這樣做可能會誇大你的發現的重要性。如果你失敗了15次,成功1次,然後在統計的時候不提那15次失敗,這樣數據上看起來你的結果就很重要,但這事實上是一種誤導。統計的時候應該要把所有做過的實驗算在內,不能只算那個成功的實驗而已,尤其在社會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我們看到很多傷害就是因為大家只報告成功的部分,而且講述故事的時候把整個實驗過程直接導向成功的結果所致。
當需要將自己的工作傳達給大家知道的時候,科學家自己本身是不是最大的絆腳石?
喬許.佛爾:像我這樣的人其實不一定要出現在溝通的過程中。理想上,科學家可以是很棒的溝通大師,而且在溝通過程中其實不需要非專家介入把科學家做的事組合成有條理的故事。
詹姆斯.葛雷易克:不過研究和溝通的技巧不一定會相伴發生。你可以是一名偉大的科學家,同時缺乏絲毫想溝通的興趣。牛頓就是一個不怎麼樣的溝通者(communicator)。我覺得我們應該只要慶幸能有像布萊恩‧格林恩這類的人,可以身兼偉大的科學家和溝通大師二職。我想這樣的人應該大多是例外。
喬許.佛爾:不過我很好奇,在溝通方面比較優秀的科學家,是不是在科學研究方面就比較不出色?
布萊恩‧格林恩:有些人是真的這麼覺得。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有個新機構,想把科學傳播作為科學研究生訓練的一部份。對我來說,這看起來很合理,如果人們可以進行比較自由、條理清晰的溝通,即使只發生在科學家之間,也可以激發更多的點子。
喬許.佛爾:在科學書籍或是一般文章裡頭要做的事就是去蕪存菁,找出精華的部分,然後傳達給其他人。這不只是講故事而已,這需要思考以及清楚的溝通。不只是科學家,整個學術界的溝通逐漸缺少條理清晰的特色,而且我覺得這讓他們的思緒比較不清晰。
平克和格林恩,你們覺得學術界的同事會因為你寫一般書籍所以比較不看重你嗎?
布萊恩‧格林恩:一開始的時候我的確有這樣的顧慮,至少在我寫第一本書的時候。不過我發現至少在表面上,大部分弦論領域的人覺得他們陷在這個沒人知曉的科學小角落,所以他們喜歡向大眾推銷弦論的想法。
史迪芬.平克:我的經驗跟他一樣。我不想讓自己的思緒一直圍繞在這種事上頭,要不然我就會很輕易找些藉口,把那些批評我的人轟開,也會給自己藉口不認真看待那些我身為一名科學家應該要認真看待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