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荒謬與反抗系列作品全集套書:荒謬系列四部曲《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卡里古拉》《誤會》+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反抗者》《正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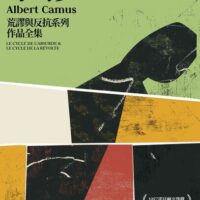
- 書名:卡繆荒謬與反抗系列作品全集套書:荒謬系列四部曲《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卡里古拉》《誤會》+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反抗者》《正義者》
- 作者:卡繆
- 出版社: 大塊文化
- 出版日期:2022/02/24
- ISBN:
★本套書內含:
卡繆荒謬系列四部曲《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卡里古拉》《誤會》+
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反抗者》《正義者》
卡繆在他的札記裡規畫其創作預計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荒謬」系列,第二階段是「反抗」系列,第三階段是「愛」系列。可惜卡繆在第三階段創作初期便因車禍過世,第三階段的作品只有小說《第一人》的殘稿,完整完成的只有前兩階段「荒謬」與「反抗」系列的作品。卡繆的每個系列創作都是以「小說」、「論述/散文」、「戲劇」三種類型三管齊下:小說訴求描繪有情節能深入內心,論述要工整有條理爬梳資料,戲劇則可以直接呈現情緒、對話攻防、直指人心,以三種不同的類型創作呈現同一母題的思考。卡繆的創作是文學界思想界難得的展現,可以見到作者以不同作品相互延伸、拓展、論證,見識到大師級創作者的多元思考。
卡繆在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異鄉人》、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戲劇《卡里古拉》與《誤會》。
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
《卡繆荒謬與反抗系列作品全集》將卡繆完整創作的兩套作品系列,特邀熱愛卡繆作品的法文譯者名家嚴慧瑩翻譯,逐年累積終於全套作品竣工,得以讓中文讀者用最貼近現代的語彙,以卡繆規畫的兩階段三類型七作品的方式閱讀,體驗卡繆如何透過這些作品互相支援互相辯證,完整呈現作家的創作概念。
「作品展現出高度清透澄淨,具穿透力且精細,以及法語文學的獨特藝術。⋯⋯他所用的藝術,透過一種全然經典的純粹風格,把存在景況的問題體現出來,讓人物和行動把他的意念活生生呈現在我們眼前。」——安德斯.奧斯特林(Anders Österling),詩人、瑞典學院常務祕書,諾貝爾獎頒獎獻辭
「我們必須朝著真理與自由前進,雖艱辛卻充滿決心。在這漫長的道途上,會感到疲憊和退縮,然而我不會忘記陽光和活著的樂趣,以及我成長於其中的自由。」——卡繆,〈諾貝爾文學獎典禮致詞〉
《卡繆荒謬與反抗系列作品全集套書》包含:荒謬系列四部曲《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卡里古拉》、《誤會》,與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正義者》、《反抗者》
荒謬系列四部曲:
《異鄉人》 L’Étranger (小說,1942)
《薛西弗斯的神話》 Le Mythe de Sisyphe (散文/論述,1942)
《卡里古拉》 Caligula (戲劇,首版1944,定版1958)
《誤會》 Le Malentendu (戲劇,1944)
反抗系列三部曲:
瘟疫 La Peste (小說,1947)
正義者 Les Justes (戲劇,1949)
反抗者 L’Homme Révolté (散文/論述,1951)
《異鄉人》
他對別人與世界沒有意見,也不說空話,
然而他的誠實,卻變成邪惡靈魂的罪證。
莫梭是住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年輕人,他意外槍殺了一個阿拉伯人,被逮捕候審。這原本是一樁相對單純的案件,卻因為夏季沒什麼大新聞,就被炒成報紙上眾所矚目的大事。
莫梭平常與人保持距離、不空口說話的個性被挖出來當作反社會人格的證據;把母親送到養老院、母親過世時沒有哭泣,變成毫無良心的鐵證;在守靈夜喝咖啡抽菸,更讓人合理推斷他是個禽獸不如的傢伙。檢察官表示,被告在精神上殺死了母親,是社會敗壞的根源,請求法官判處極刑。然而,始終沒人談論那個被殺害的阿拉伯人⋯⋯
《異鄉人》展現了卡繆對世界的敏感認知。世界的荒謬性來自個人想法與現實的落差,但現實卻是奇妙的人心所構成,是眾人構成世界的荒謬。這本小說簡短卻異常有力地表現出人類社會的特性,直到今日都還切中人心。
卡繆的初試啼聲之作便受到矚目,《異鄉人》出版於一九四二年法國被占領時期,是他規劃自己第一個創作階段的起始。卡繆規劃的第一階段為「荒謬」系列,作品包括小說《異鄉人》、散文《薛西弗斯的神話》、戲劇《卡里古拉》和《誤會》。《異鄉人》是最受歡迎的作品,據統計截至二〇一一年為止,光是在法國的累計銷售量就超過了一千萬冊,是改變戰後法國文學歷史的重要作品。
「《異鄉人》是一部經典作品,是有條理的作品,寫到有關荒謬同時對抗荒謬。」——沙特(Jean-Paul Sartre),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我在莫梭身上看見一些正面的東西,那就是他至死一直拒絕說謊。說謊不光是說不真實的話,也是容許自己去說所知以外的東西,主要是為了順從社會。莫梭不是站在法官、社會法律或傳統感覺的一邊。他的存在就像在太陽下的一塊石頭,又或像風和海,這都是永遠不會撒謊的東西。」——卡繆
《薛西弗斯的神話》
真正嚴肅的哲學議題只有一個:自殺。
人生因為有意義才值得活?人是因為洞悉活著的無意義才能幸福地活著!
只要蔑視命運,就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被克服的。
「幸福和荒謬是同一塊土地的兩個兒子,二者無法分開。
若說幸福必定是從發現荒謬開始,是錯誤的;
但有時,荒謬的感覺是來自幸福。
保持清醒洞悉折磨著人,卻也同時是人的勝利。」
——卡繆
薛西弗斯被神處罰推著大石上山,然後石頭滾下,他得走下山再把石頭往上推,再滾下⋯⋯這種日復一日的徒勞,彷彿是現代人生活困境的寫照。
在這充滿厭世感的時代,種種人生困境,是我們身在其中而難以跳脫的。這類的厭世感與荒謬感,起源於自我認知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落差,但這種落差是必定存在的,所以荒謬會一直存在。
既然荒謬是必定存在的,那人生可以怎麼活?或者,人生值得活嗎?
卡繆認為,判斷人生值不值得活,人要不要為此自殺,是唯一嚴肅的議題,其他的哲學考量都是次要的,必須先來好好面對這實際而難纏的問題。
卡繆帶我們去思考過往哲學思考者對於生命困境的理解,尤其是對宗教的寄託,他認為宗教給的是對來世的美好寄望,其方便的解答,使人感到溫馨懷念。這種解答讓人不必費力推敲,只要不加思考地相信,彷彿就可以解決苦惱。但這種寄望是虛假的,在此世無法證實,但卻使人因為不加思考而接受擺佈,反而更像是被迫推著巨石卻不明所以的人。
卡繆在本書透過情聖、演員、征服者幾種人生類型,去展現人即使知道最後必會面臨死亡來勾消一切,而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當下的生命。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剝奪的,只有自己能夠決定怎麼讓自己的生命充滿熱力。生命不會是永恆,也就沒辦法達到過往以為的唯有永恆才是有意義,反倒是因為不受限於「意義」的束縛,才更能好好地活著,好好地體驗自己這獨一無二的人生。
是以,卡繆說:荒謬是必然的,而與荒謬的奮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
《卡里古拉》
人們都以為人會痛苦,是因為所愛的人死去。
其實真正的痛苦並非這麼淺薄,
而是發現悲傷也不會持久,連痛苦都失去了意義。
羅馬歷史上的卡里古拉是個暴君,建立恐怖統治,將自己神化、行事荒唐、大肆鋪張、任意殺害人命。他增加各種苛捐賦稅、謀奪人民財產來解決國庫危機,行事不定引起臣民疑懼與怨恨,最後卡里古拉被刺殺而亡。
卡繆以此羅馬帝國的歷史故事為底本,創作四幕劇《卡里古拉》來描摹人世的荒謬性。卡里古拉一開始是個頗獲民心的皇帝,但在他的妹妹兼情人圖西菈死後,他認為世界就是無法讓人順遂的,因此性情大變。此後他就充滿鄙夷和憎惡的情緒,要將皇帝的權力推到極限來顛覆一切,向友誼、愛情、親情等人類認為良善的價值觀挑戰。他狂熱的破壞性把一切帶入凶險,最後也毀滅了自己。
這齣戲表面看起來是歷史劇,以羅馬帝王故事呈現令人不解的暴政。但更深一層,卡繆試圖將他的荒謬哲學放入史實,塑造一個謎樣且讓人不斷思索的角色,以荒謬哲學來貫穿歐洲世界自古以來思索的生死、自由、權力、毀滅等議題。卡里古拉在心愛的人死後,面對價值觀的衝突,面對自己身為人的局限,試圖以權力拓展限制,將皇帝的權力無極限濫用,甚至扮演神明,認為這是人的最大自由。
這種試探,也是卡繆在其荒謬哲學中反覆思辨的,人類以必朽的肉身與有限的力量,如何對應幾乎無法撼動的世界,該怎樣面對生命意義的匱乏。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辯證人是否該因生命無意義而自殺,而卡里古拉在卡繆的劇場中,成了卡繆自身黑暗面的化身,以戲劇行動去試探界限,終究因無節制的暴力而招來自身的毀滅。
此劇發表時是在二戰剛結束後,暴政對應的是法國人剛結束的納粹統治,以及維琪政府時期的通敵狀況。這種時代氛圍使得人們看待《卡里古拉》眼光就不純粹是歷史劇或哲學劇,或許卡繆當初心裡想像的荒謬哲學劇作,也跟隨後出版的《瘟疫》一樣,成為反省納粹時代、反省極權的重要作品,深刻影響著後世。
《誤會》
犯罪是一種孤獨,就算一千個人一起動手也一樣。
孤獨地活、孤獨地殺人,現在孤獨地死,這是應當的。
《誤會》是卡繆作品中最簡單易懂也最聳動的創作。卡繆從《阿爾及爾回聲報》上讀到一則報導,這新聞撼動了他,因為在這個事件裡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因此寫下了《誤會》,這個故事也在小說《異鄉人》裡以剪報的形式登場過。
小說《異鄉人》裡的剪報版本是這樣:一個男人離開捷克小村到外地闖天下。二十五年後,賺了大錢,帶妻兒回故鄉。她母親和妹妹在家鄉開了旅店。為了給她們驚喜,他將妻兒安置在另外一家旅館,自己到母親的旅店去。他進門時,母親並未認出他來。他想開個玩笑,便突發奇想訂了個房間,還亮出錢財。夜裡,母親和妹妹殺了他,偷了錢財,把屍體丟到河裡。到了早上,他的妻子來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出了旅人的身分。母親上吊自殺,妹妹投井自盡。
這個故事必然糾纏著卡繆,讓他在小說裡的簡單描述外,再度發展這個主題,添加血肉創作成完整的三幕劇:返鄉的旅人與多年不見的母親和妹妹相互試探,旅人在不說破身分的前提下試圖與她們交心,不知情的母親與妹妹決心謀財害命,但她們為了避免殺人良心不安而拒絕多認識旅人。在多重誤會之下,母女倆迷昏了自己的親人,奪取金錢,將其丟入河中溺斃⋯⋯
這個故事刺痛了卡繆的心,這來自於他從北非到法國流徙生涯的恐懼,也因為他把母親留在阿爾及爾前往巴黎的罪咎感。他曾寫到,像自己這樣的一個孩子,人生整個觀感都由他與母親的關係而界定。也因為《誤會》這個故事對卡繆意義重大,他在兩個作品裡都寫到它,但卻用了相異的手法來呈現:《異鄉人》的主角莫梭被檢察官和媒體控訴形同謀殺了母親,而《誤會》裡的故事則是母親殺死了兒子,像是對映的兩面,顯現出卡繆思考人類荒謬處境的最佳案例。
《誤會》是卡繆自我定義的作品,也是他不得不寫的重要創作,更是進入卡繆荒謬思考領域最簡單也最深刻的辯證。
《瘟疫》
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逼我們去思考。
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也會出現在瘟疫中。
面對這樣的瘟疫,人們該奉行的唯一口令是反抗。
卡繆的《瘟疫》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每當疫疾來臨,這本書總是最早被拿出來討論的現代文學作品之一。但卡繆不只描寫瘟疫,也將面對瘟疫時人類由一開始的抗拒、否定,之後確認,最後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處境,踏實地將圍困人類的瘟疫加以處理。這太像我們經歷過的一切,先是抗拒疫情,接著否認會大規模人傳人,等到狀況嚴重了,不得不確認遇到大疫,接著才願意誠實面對困境加以處理。經典作品就是有如此的價值,跨越時代反映普世人類,也時時提醒著我們。
《瘟疫》的故事描述一九四幾年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城,一位醫生發現城裡有不明的疾病,察覺很多老鼠倒斃路旁,開始懷疑城裡有了鼠疫,上報給政府機關,但政府機關卻不想因此驚動人民,遲遲沒有作為。後來疫情爆發,整個城市封鎖,與外界隔離,小說中的幾位主要角色的邊緣小人物(相對於有權力的官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防疫工作。《瘟疫》的故事展現了認識世界的荒謬之外,必須要站出來加以反抗,才能爭取到自己的幸福。小說裡還提到:「追求幸福沒什麼可恥的,但是獨自一個人幸福,就可能會讓人覺得可恥。」標示出這種對幸福的追求,不是個人小利,而是全體的幸福。
《瘟疫》與《反抗者》、《正義者》同屬於卡繆同一創作時期的作品,卡繆在其札記中稱為「反抗系列」,這系列的三部曲作品以小說、論述、戲劇等三種文類,反覆辯證人類與惡對壘的反抗精神,訴求個人認知上的反抗,面對過分的事物要勇於畫出底限,說不。
卡繆在一九四〇年創作《異鄉人》時有了寫作《瘟疫》的靈感,當時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法國,他隨著任職的《巴黎晚報》遷移到克萊蒙費朗,再到波爾多,這種被迫逃難、遷徙、被圍困的感受成了他的靈感。《瘟疫》一方面是真實發生在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奧蘭城的斑疹傷寒,一方面指涉的是入侵法國的德國納粹法西斯政權;傳染病讓人類不得不封鎖彼此,對彼此懷疑,就像法西斯政權,也讓原本自由的人們彼此疑忌,在行動上也被限制、被封鎖。這部小說利用一個城市被疾病困擾的故事,表達一個超越於荒謬的反抗願景:在對抗邪惡的鬥爭中團結的可能性,以及友誼和社群的力量。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者》
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
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
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常被認為是提倡荒謬思想的大師,但這種簡化的描述只搆得到卡繆的創作初期。這位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文學大師,面對世界劇烈變動的景況,無可避免地去探究為何文明的發展卻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他的作品《異鄉人》及《薛西弗斯的神話》思索個人面對生命的處境,因理想和現實的落差造成了荒謬感,以及個人如何面對這種荒謬。對人世充滿熱情的卡繆並不滿足於此階段的答案,他接著更進一步去討論,從個人進到與他人的關係、人類群體社會時,該又如何面對群體生命的挑戰,是更入世、更社會性的思考。
《反抗者》是卡繆處理個人與社會群體關係的重要著作,思考著人類社會巨大的難題:
人要脫離被奴役的身分,便必須反抗,被逼迫到一條界限時,要站出來說「不」。
如果為了反抗不義,是不是可以用盡任何手段?
若為了遠大的目標,是不是就該犧牲一切,即使是必須殺人?
反抗與革命之後,如果建立起來的社會又形成另一種壓迫專橫,該如何解決這難題?
這是卡繆處理對二十世紀巨大的法西斯政權和共產主義專政的思索,特別是後者一度被認為是人類未來社會的希望,在卡繆的時代許多思想家都熱烈擁護,但現實卻證明其墮落,如同卡繆所說的陷入虛無主義的毀滅。而從二十世紀後半的冷戰到今日,人類社會的挑戰還是籠罩在卡繆的這個思辨裡,只是當下盤據人類社會上空的權力幽靈,從政治權力轉為力量更加綿密無孔不入的經濟政治綜合體,帝國的勢力時時刻刻影響我們的生活。從專制體制紓解出來不久的人們,脫離了政治力的箝制,卻又面對了更嚴峻的考驗。
為此,思索反抗對當代的我們更形重要,如何反抗但卻不致於形成全面毀滅的虛無,或者避免反抗之後卻建立起另一座牢籠。
卡繆的推敲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永恆提醒。
《正義者》
卡利亞耶夫和他全世界的弟兄們拒絕神化自己,
因為他們拒絕剝奪別人生命的過度權力。
學習生存與死亡,想要成為人,就要拒絕成為神。
《正義者》是一齣五幕的戲劇,卡繆改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黨人行刺謝爾日大公的故事。大學生卡利亞耶夫反對俄國帝制統治,想尋求革命,他與同伴計畫以炸彈刺殺謝爾日大公,試圖動搖專制體制。第一次的行動因為謝爾日大公車上有無辜的孩童在,因而緊急取消,卡利亞耶夫認為即使革命重要,卻也不應該犧牲無辜的人,也與他的夥伴對此產生激烈辯論,討論為了正義的理念是不是可以不擇手段。之後卡利亞耶夫與同伴找到另一個機會,炸死了大公,但也因此入獄。大公夫人前去獄中與卡利亞耶夫對話,要他供出同黨,就可以換得赦免。卡利亞耶夫拒絕了,之後從容就義。他殺了人,雖然是有著更遠大的理念而殺人,但不以此理念為藉口,而以自己的生命付出代價成就正義,戰勝了歷史上種種想要站上神壇的虛無主義。
卡繆非常重視這段故事延伸出來的意義,在《反抗者》裡也加以討論。卡繆寫道:
「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生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在認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認為暴力是不正當的,殺人是必需,但不可原諒。」
「他們認為不得不然的行動,卻又難以自我說服,就想出奉獻出自己來合理化一切的辦法,以犧牲自己生命來回答對自己提出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如同對他們之前所有的反抗者一樣,殺人也就代表自殺,以命抵另一命,在這雙重犧牲之中,或許會滋生出一種價值。卡利亞耶夫、瓦納洛夫斯基和其他同伴相信每個生命都具有同等價值,沒有任何理念凌駕於人的生命之上,儘管他們為了理念而殺了人。他們身體力行這個理念,乃至於以死來實現它。」
《正義者》以歷史事實化身的人物,透過情感和對話表現出卡繆認為的反抗精神,標誌出誠實與責任的反抗意識,並非有理念的反抗便可以犧牲他人,唯一可以犧牲的只有自己,這部劇作也是卡繆對於真正的正義反抗所表達的敬意。
作者簡介
卡繆(Albert Camus)
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家庭,父親在他出生未久便被徵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身亡,幼小的卡繆被母親帶回娘家撫養。中學以後卡繆開始半工半讀,做過很多工作,雖然生活辛苦,但阿爾及利亞臨地中海的陽光普照溫暖氣候,對卡繆的思想及精神有深刻的鼓舞,後來更成為他思想體系的象徵,相對於德國思想家所產生的北方思想。
卡繆大學畢業後先擔任記者,報導許多阿爾及利亞中下勞動階層及穆斯林的疾苦,同時參與政治運動,組織劇團表達觀點。二戰爆發後因在阿爾及利亞服務的報紙被查封,於是卡繆前往巴黎的報刊任職。在阿爾及利亞時卡繆便開始創作戲劇、小說與散文,一九四二年出版《異鄉人》之後開始在法國與國際獲得推崇,一九五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讚其作品:「具有清晰洞見,言詞懇切,闡明當代人的良心問題。」卡繆在一九六〇年於法國車禍驟逝。
卡繆的作品多樣,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有:小說《異鄉人》、戲劇《卡里古拉》和《誤會》、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有: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其他小說作品有:《墮落》、《快樂的死》、《放逐與王國》,與遺作《第一人》,以及戲劇《戒嚴》、改編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戲劇《附魔者》等。
譯者簡介
嚴慧瑩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當代法國文學博士。目前定居巴黎,從事文學翻譯。譯有卡繆作品:《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誤會》、《瘟疫》、《反抗者》、《正義者》,韋勒貝克作品:《血清素》、《屈服》、《無愛繁殖》、《情色度假村》、《誰殺了韋勒貝克》,以及《六個非道德故事》、《緩慢》、《羅絲‧梅莉‧羅絲》、《永遠的山谷》、《沼澤邊的旅店》、《如果麥子不死》、《灰色的靈魂》、《落日的召喚》、《地獄之門》、《野性的變奏》、《我,們》、《獨子》、《ROM@》、《調查》、《我生命中的街道:佛朗克的巴黎記憶》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