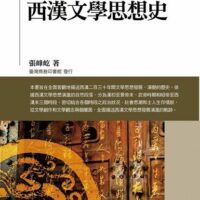西漢文學思想史
描述西漢230年間萌芽狀態的文學觀念其發展歷程。把握其文學觀念演變的自然脈絡,揭示各個發展階段的特點,並努力描述出這二百三十年間文學觀念的發展趨向和總體特徵,確定其在中國文學思想發展史中的歷史地位。
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歷時長久的一統王朝(秦雖統一中國,但是僅有十五年的國運),它的建設和發展,較之以往,有著新的內涵。春秋戰國時期,政治失序,沒有權威,思想文化百花齊放,多恣而繁榮。短壽的秦王朝,在政治建設上雖有貢獻,但倏忽十五年間,政治統治不及完善,文化的整肅或發展更未暇顧及。西漢王朝所繼承的,就是這樣一份失序又繁榮的政治、文化遺產。鑒於戰亂初定、經濟崩潰、百廢待興的實際,劉漢統治集團最初採取了清靜無為、輕刑減賦、不擾民耕的策略,以圖復蘇經濟、發展生產並穩定政局。與此同時,在政權建設方面,以退為進,從隱忍中謀專制。這便引導和鼓勵黃老之學大興于漢初。隨著經濟的復甦和發展、異己勢力的漸被消除,皇權也就漸漸抬頭。到景帝初年,以「七王之亂」被翦滅為標誌,西漢王朝的集權政治開始確立。與之相伴隨的,便是顯赫近七十年的崇尚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行將退出歷史舞臺。到武帝即位,獨裁政治的時機已然成熟,這個歷史上頗有作為的帝王便毫無顧忌地實行一姓專制了。他「外事武力,內興功業」;在思想文化領域,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表象,大行「以儒術緣飾吏事」之實際。儒學越出於百家之上獨自顯達了,同時也遭受到從未有過的無奈。這樣的政治、文化狀況經歷了五十年之後,歷史又發生了變化。自昭帝初年到西漢末,政局動盪多變,外戚、中宦、權臣交替專權,皇權在總體上呈示為衰落的局面。一個有意味的現象卻是,在武帝首倡「獨尊儒術」時代未曾真正尊顯的儒學,到西漢後期卻大盛起來。昭帝初年召集的鹽鐵會議,奠定了儒學興盛的根基;宣帝末年召集名儒討論《五經》同異的石渠閣會議,以其有眾多碩儒的參與和宣帝親臨決議的待遇,更使儒學燦發出從未有過的光芒。但是,在專制的時代,政治才具有決定生死存亡的最高權威。西漢後期的一個多世紀,像宣帝這樣皇權專制的情形,只不過維持十餘年而已(宣帝前期還是霍氏專權);絕多的時間裏,乃是外戚交替擅權的軍人政府執政。於是,在這一時期,儒學的地位便十分尷尬:一方面是地位被空前提高了,如太學生的數量極大增加,全國各地各級行政區域廣設教習經學的學校使之極大普及,風靡上下的災異論政思潮,儒生中有多人位至三公之職;另方面是儒學又受到空前輕視和宰割,一個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儒生頻遭貶廢囚殺,有時一次殺戮即百餘人!或是上千人被視為異己而遭排斥。在此種情形下,到西漢末年,隨著儒士的疏離政治,道家思想又復歸思想界。因此,西漢後期,思想文化的發展趨勢,便呈現為本儒兼道、由儒而道的走向。
在上述道、儒嬗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西漢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觀念也隨之浮沉俯仰。從高祖初到景末武初,是西漢文學觀念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在創作傾向上,從賈誼辭作的濃情質實到枚乘賦作的失情華麗,反映出這一時期文學觀念的多元並存及其發展趨向;而體現在四家《詩》解、子書、政論以及《淮南子》中的文藝觀念,也與這一時期的創作傾向基本吻合,共同呈示著道儒交糅、重情尚用的特徵。自武帝初至昭帝初的約五十年間,是西漢文學觀念發展的第二個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呈現為兩種情形:一是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大賦創作,由於皇權極盛下儒學的「緣飾」地位和士人的俳優或類俳優地位,再加之以大賦體制上鋪排誇飾、艱澀繁辭、喪失真情的特色所決定,使大賦在諷諫上表現出意圖和效果的相悖情形,從而實際地顯示著逞才遊藝的特徵;二是東方朔、司馬遷、董仲舒以及孔臧等人的非大賦(小賦、辭)創作,或直抒胸臆,情真意切,或詠物托志,感慨誠愨。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無論是大賦的逞才遊藝,還是非大賦的抒情、詠物,都是文學觀念極大發展的表徵。在這一時期的經學文獻中,也可見出文學觀念的某些內容。《詩大序》和《禮記·樂記》,都是這一時期最終寫定的文獻,情志與教化並重,詩樂與政教共說,不僅是它們的共同特徵,顯示著西漢文學觀念的主要特色,也同時是前此儒家文藝觀念的集成;董仲舒所提出的「《詩》無達詁」和「中和之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具有創新品質,但它同樣還本是經學的思想,初不為文藝而發。我們在挖掘它文學理論的涵義時,充分注意了這一特點。武帝時期最值得稱賞的,是司馬遷的著述思想——「發憤著書」。考之司馬遷的家族出身和他一生的遭際,再衡之《史記》的寫作實際,便可發現「發憤著書」實有兩重涵義:一是基於其孝祖情結和聖人情結之上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這一意義上可以釋之為「發奮」;二是緣於不平慘怛的身世遭際以及歷史家高瞻遠矚縱觀歷史的深刻認識而產生的一種歷史憂患,在這一意義上可以釋之為「發憤」。因此,司馬遷「發憤著書」的著述思想,不唯「坎坷人生造就成功創作」一層意義而已。總觀武帝時期的創作和經學文藝觀念,總體上與當時的社會思潮相一致,即呈現著儒家精神。從昭帝初到西漢末,是西漢文學觀念發展的第三個時期。這一時期,又可以元、成之際為界限,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創作上的代表作品就是揚雄的五篇大賦,基本上是對司馬相如的摹仿(但在寫作上已有了新的發展)。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揚雄初仕時昂揚進取心態的表現。另外,王褒將仕前夕所制的《中和》、《樂職》、《宣佈詩》以及配套的《四子講德論》,劉向的多次上書言說政事,都是西漢後期之初儒學極大昌盛的反映。而劉向、翼奉、匡衡等人的經學思想中所呈示出來的文藝觀念,更是體現著經學對文學思想的深入滲透。到了後一階段,情況就有了新變。隨著士人對政權的不斷疏離,道家思想回歸思想界。做為這一變化的前兆,王褒寫於宣帝末年的《洞簫賦》,已經啟動了文風的變化(儘管此作還有教化的尾巴,也還有鋪誇的痕跡);而揚雄、劉歆、班婕妤等人的小賦和辭作,更著實地表現出這一階段回歸自我、重視抒情、不求華贍的創作傾向。作為這一階段文學思想的主要體現者,揚雄本儒兼道的文學觀念,正是西漢後期文學觀念本儒兼道、由儒而道發展趨向的縮影。
簡要地歸納西漢二百三十年間文學思想演變的歷史,是沿著道儒兩種思想交叉、交替、發展演進的歷史,由道(黃老)而儒,又在一定程度上回歸道家。